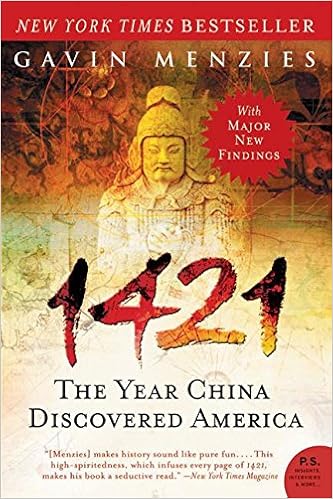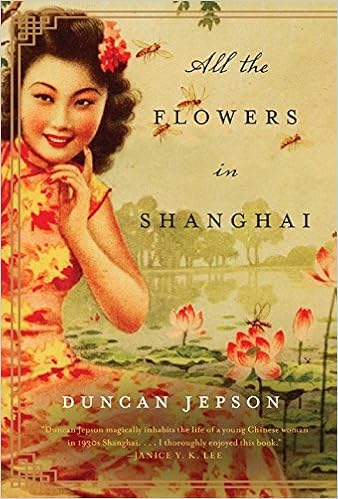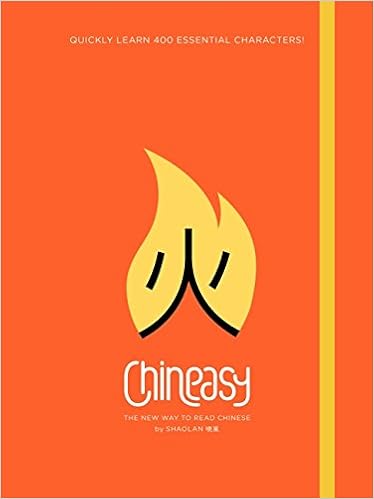By Gao Hua
Yan'an Rectification circulation was once the foremost occas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chinese language ancient development, which used to be the 1st large-scale political circulat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st celebration led through Mao Zedong himself, and the start of political campaigns. Mao Zedong use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2 methods of reading the cadres' own histories and response purge created through himself in Yan'an Rectification, absolutely got rid of the impression and stay deliberating the may possibly 4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the get together, thoroughly cleared switched over CPC "Russification" temperament, rebuilt the higher constitution of Mao Zedong as totally ruled, laid the final beginning of the occasion for Mao Zedong, in which a chain of techniques, paradigms replaced the existence and the destiny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language humans after 1949.
Read Online or Download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PDF
Best China book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On March eight, 1421, the biggest fleet the realm had ever noticeable set sail from China to "proceed the entire opt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o assemble tribute from the barbarians past the seas. " whilst the fleet again domestic in October 1423, the emperor had fallen, leaving China in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haos.
All the Flowers in Shanghai: A Novel
“Duncan Jepson magically inhabits the lifetime of a tender chinese language lady in Thirties Shanghai…. I completely loved this e-book. ”—Janice Y. okay. Lee, ny instances bestselling writer of The Piano Teacher“Breathtaking…. a superb paintings that may flow its readers. ”—Hong Ying, overseas bestselling writer of Daughter of the RiverReaders formerly enchanted by way of Memoirs of a Geisha, Empress, and the novels of Lisa See might be captivated through Duncan Jepson’s superb debut, all of the plant life in Shanghai.
Chineasy: The New Way to Read Chinese
Learn how to learn and write chinese language with Chineasy—a groundbreaking technique that transforms key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s into pictograms for simple keep in mind and comprehension. chinese language is without doubt one of the oldest written languages, and the most tricky to grasp, particularly for Westerners. With Chineasy,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language hasn't ever been easier or extra enjoyable.
China A to Z: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stoms and Culture
A realistic and obtainable advisor to an historical yet quickly altering culture—now revised and updated Perfect for company, excitement, or armchair tourists, China A to Z explains the customs, tradition, and etiquette crucial for any journey or for somebody desirous to comprehend this complicated nation. in a single hundred short, reader-friendly essays alphabetized through topic, this absolutely revised and up-to-date version presents a crash direction within the etiquette and politics of up to date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nation’s geography and venerable heritage.
Additional info for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Edu. hk Web-site: www. chineseupress. com revealed in Hong Kong listing 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重印自序 上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二、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三、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五、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六、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二、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三、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四、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二、毛澤東的理論攻勢與劉少奇對毛的支持 三、讓步與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 四、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第四章 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二、關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三、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四、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麽? 二、「挖墻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下編 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二、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三、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四、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五、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雲、李富春 六、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的崛起 七、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係:處境尷尬的軍方 第七章 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一、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二、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三、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一、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麽? 二、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第九章 從「延安之春」到斗爭王實味 一、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毛澤東與延安「自由化」言論的出籠 二、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王實味言論中的意義 三、風向突轉:毛澤東拿王實味開儀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延安文化人套上「轡頭」? 五、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毛澤東「黨文化」觀的形成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傳和幹部教育系統的重建 一、重建「黨的喉舌」:延安《解放日報》的整風 二、陸定一、胡喬木與毛氏「新聞學」原則的確立 三、鄧發被貶黜與中央黨校的三次改組 四、彭真與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第十一章 鍛造「新人」:從整風到審干 一、教化先行: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 二、排隊摸底:命令寫反省筆記 三、審查在後: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四、為運動重心的轉移作準備:毛澤東、康生的幕後活動 五、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歷史 六、「脫褲子,割尾巴」:在雙重壓力下滌蕩靈魂 七、「得救」:「新人」的誕生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一、康生機關與1937年後延安的「肅托」 二、1940年的審干與幹部檔案制度的建立 三、「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反奸(肅反)」 四、毛澤東的「肅反」情結: 五、毛澤東、中央總學委和中央社會部的關係 六、在「試驗日」裏制造出的「張克勤案」 七、「搶救」的全面發動與劉少奇進入「反奸」領導核心 第十三章 「搶救」風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據地 一、「搶救」的策略和手段 二、中直機關的「搶救」 三、軍直機關的「搶救」 四、西北局和邊匾系統的「搶救」 五、中央黨校的「搶救」 六、延安白然科學院的「搶救」 七、魯藝(延安大學)的「搶救」 八、晉察冀、晉綏、太行根據地的「搶救」 九、華中根據地的「搶救」 十、唯一未開展「搶救」的山東根據地 第十四章 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一、「審干九條」再頒布後「搶救」為什麽愈演愈烈? 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三、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四、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第十五章 「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 一、「毛澤東主義」的提出與修正 二、劉少奇等對毛澤東的頌揚 三、摧毀「兩個宗派」: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 四、修訂《歷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體系 五、中共七大召開及博古、張聞天等人的公開檢討 六、毛澤東的勝利與中共新的領導核心 後 記 參考文獻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書刊一覽 更多書籍 前 言 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一幕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由于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范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 黨內上層的斗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 全黨的思想改造; 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 新制度的創設。 在上述幾個方面中,黨內上層的斗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發端于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于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于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面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并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面向王明發起挑戰,并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于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沉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與范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經過多年的斗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造成歷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于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于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輸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于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面對復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制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復蘇,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有意放縱其專斷的個性,使之有機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層,毛澤東以我劃線,創造并利用一切機會打擊異己;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毛澤東策動整肅全黨幹部的「搶救運動」,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澤東植入中共肌體的極左的審干、肅反政策,經過整風運動,演化為黨的性格的一部分,對1949年後的中國帶來長期不良的影響。 延安整風為毛澤東顯現其復雜詭奇的政治謀略提供了舞臺。毛澤東敢于突破中共歷史上的常規,其手法深沉老辣,對其對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敵謀略的運用,均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地步。毛澤東的謀略既來之于他對中國古代政治術的熟練運用,又源之于他對俄共「格伯烏」手段的深刻體會。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面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驁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峭刻嘲諷,由于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面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瞭解。 發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但是在傳統意識形態術語的演繹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書的目的,并不在于對主流話語系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而是試圖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對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新的研究,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斯是吾愿,是否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待讀者評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2000年3月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兩年來,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對于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延安整風運動是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但學界的相關研究卻較為薄弱,我在本書中嘗試性對其作出研究和分析,自是一家之言,歡迎讀者隨時賜正為禱。 此次拙著重印,特別要感謝一些學界前輩的指教。楊振寧、王元化、陳方正、吳敬鏈、韋政通,張灝、林毓生、張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與我探討拙著中涉及的若干重要問題,并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寶貴的鼓勵和嘉許。金觀濤、劉青峰、熊景明、呂芳上、陳永發、劉小楓、許紀霖、蕭功秦、朱學勤、何清漣、陳彥、丁學良、徐友漁、黃英哲、唐少杰、錢文忠、錢永祥、梁侃、毛丹、李楊、張文中、錢鋼、吳東峰等先生還就我所從事研究的如何深入發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書初版時,由于電腦轉換簡繁體字的功能不盡完善,雖然對文稿做了多達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干文字的錯誤。此次重印僅限于文字錯訛處的更正。近兩年來,圍繞延安整風運動,又有若干新的史料問世,日後,當拙著出增訂本時,我將對其內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補充。 在這裏,我要對殷毅、馬沛文、尉天縱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馬沛文先生就來信、他們不僅就拙著的內容和寫作與我進行了深入地討論,還特別指正了書中的文字錯誤。尉天縱先生也來信指正了書中一誤值的地名的錯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專家,她的語言學方面的知識對本書的修訂有重要的啟發。 本書的修訂,由我的研究生黃駿協助做了電腦文字處理工作,特此致謝。 高 華 2002年5月12日于南京龍江寓所 上 編 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裏,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他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于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盡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辟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他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係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權限關係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1-1]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于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并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并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系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斗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後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幹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1、「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1-2]。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1-3]「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1-4]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于根據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于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系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于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1-5]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麽樣兒,是一回什麽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麽事。」[1-6] 盡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只是提出黨的農民成分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于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游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瞭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擔心。毛認為盡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于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只占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于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于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并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面對現實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2、「軍黨」的問題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後,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采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10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入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制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采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于9月重新占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系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于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復雜的。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係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分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分上盡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分,減少流氓的成分」,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1-7] 中共中央關于改變紅軍成分,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係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裏。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歷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只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3、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于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著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1-8]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後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角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1-9]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制,建立政治部體制,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權限范圍的問題終于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于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幹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1-10]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後,中共中央出于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并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于中共中央,是處于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只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只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于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辟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匯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歷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裏指手畫腳,只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并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後又發展為其他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進一步復雜化。 注釋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69。以下稱《周恩來年譜》。 [1-2]《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1-3]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82。 [1-4]《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4。 [1-5]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頁79。 [1-6]《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6。 [1-7]《中央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第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48、253、256、250、252。 [1-8]杜修經:《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頁20。 [1-9]《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載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32、136。 [1-10]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171、205—207、348、357。 二、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極左的肅反觀和復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後隨著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于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干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1-11]「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1-12]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麽1930年2月以後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1、毛澤東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于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麽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于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于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看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係親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贛西南出現了復雜的局面。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于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游擊,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于「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并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并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并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斗爭,這場斗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1-13]——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1-14]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志,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斗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後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斗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斗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斗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于「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 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1-15]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輸于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并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于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1-16]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1-17]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1-18]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于主持軍中事務,并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1-19]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斗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于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麽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并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團」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1-20]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曾在危急形勢下將被上司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有友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請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并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21]果不其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干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後,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後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1-22]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麽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根本改造」的利刃終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于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并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引致毛的極大不滿,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于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并將參加「二全會」的人一律視為「AB團」分于,列入應予「撲滅」的范圍。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1-23]這張字條究竟是何內容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系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沖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系的人相繼被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後,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領導)——(此信其實是毛澤東所寫,大陸學者為避毛諱,有意隱去毛的名字),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并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1-24] 李韶九攜毛澤東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將第二封指示信派兩位紅軍戰士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的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指示信,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實施總前委關于肅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陳正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現場指揮。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于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1-25]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團首領,并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于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1-26]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于9日離開富田)、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于8日到達)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曾山親自審訊段良弼,所得結果是抓出「A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四十余人,[1-27]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二十五人處決。 在這之前的12月9日,當總前委派來「協助肅反」的古柏趕到富田後,李韶九帶一個排警衛,押著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離開富田,于10日到達紅二十軍軍部所在地東固,立即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兩封指示信,「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劉鐵超、曾炳春根據段良弼、謝漢昌被刑訊後的口供,認定紅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是AB團分子。但因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李韶九雖然在談話中已點出劉是AB團分子,但是并沒有立即將劉敵逮捕,只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劉敵自己供認。劉敵在富田事變後,寫給中央的信中承認他在同李韶九談話後,即有了發動事變的念頭。劉敵并在信中陳述說,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制造糾紛」的人。為了躲過馬上就要降臨的刑訊逼供,劉敵改用長沙口音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只有盡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不是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三位是追是隨,我個人還有什麽呢。」李韶九見劉敵這番表態,就放劉敵回去了。[1-28] 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這天上午早飯後,劉敵同獨立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秘密開會商量應對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認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來抓AB團是打擊贛西南黨的幹部「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陰謀得逞,決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人。會後,劉敵即至獨立營對戰士進行鼓動,率領全營紅軍戰士包圍了軍部,逮捕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後逃走,軍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鄉躲避。傍晚,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軍部直屬獨立營沖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團分子」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也被捉了起來(次日即被釋放,并被邀請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亂逃出富田,跑回家鄉。古柏也從「肅反機關跑了出來」。[1-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陳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這就是震驚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劉敵等把所率領的紅二十軍帶到贛江以西湘贛蘇區永新、蓮花、安福一帶,繼續展開土地革命,并在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謝漢昌、劉敵采取了四項緊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攜二百斤黃金緊急趕往上海(實際帶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幾十兩」),[1-30]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肅AB團」及富田事變經過,請中共中央裁決。 二、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認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濫抓「AB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緝拿歸案。 三、爭取贛西南特委下屬的湘贛蘇區西路行動委員會書記王懷的同情與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澤東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率一個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貫徹總前委兩封信的精神,準備逮捕行委書記王懷,但未果)。在王懷領導下的河西蘇區、紅二十軍的反毛行動受到普遍同情,王懷的觀點——紅二十軍行動不是反革命行為,而是「工人階級路線與農民路線兩條路線斗爭」,被迅速傳播開來。富田事變當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幾十年後對此還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逐漸模糊起來」。[1-31]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的極端行為造成的影響是何等廣泛。 四、公開打出反毛澤東旗幟,并試圖爭取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支持。謝漢昌、劉敵在向贛江西邊轉移途中,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志和民眾書》,指責毛澤東有「黨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未、彭、黃」的口號。12月20日,謝漢昌、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鎮寫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信》,這封信一方面譴責李韶九大抓AB團,對同志濫捕濫殺,同時又抨擊總前委偏護李韶九,還附上了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離間毛與朱、彭、黃的關係。 《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普遍被認為是一封偽造信,當事人彭德懷的證據可能最有說服力。數十年後,彭德懷在獄中寫交代材料回憶此事時說:「這封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 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後,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歷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并進,并于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于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AB團主犯,并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10/12毛澤東。[1-32]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并《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于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會後我問鄧萍同志,公略來干嗎?鄧說,他沒說別的。只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1-33]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裏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幹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後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面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麽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麽可以呢?」[1-34]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只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干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1-35]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于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裏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斗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1-36]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2、歷時四個月的項英對毛澤東的糾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擔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擔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于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斗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1-37]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係,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并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面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面反對單純軍事游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于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1-38]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月29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後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月2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1-39]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幹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後被派往江西蘇區。 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鐘、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并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臺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份,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于1930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後,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後的歷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年11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月16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斗爭路線」;另一方面,又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係,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系AB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并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并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中主義的立場,那麽,項英針對「肅AB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斗爭中的缺點和錯誤」,并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後「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斗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1-40]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復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瞭解毛在1927年後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制止、糾正毛在「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1931年2月4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志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志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係諸同志(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後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1-41]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著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後處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月16日《決議》關于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斗爭的歷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地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辨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1-42]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他人,只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月19日後,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于下風,難以有所作為,只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并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并委派幹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係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幹部的出路只有一條:被槍斃! 3、「肅AB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斗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後,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于分裂,最後,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擔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後,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裏,有若干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年1—2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系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後,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1-43]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後,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後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後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博古等會見了他們,并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1-44]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并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 周恩來在2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兩項決定:第一、立即給江西發一中央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第二,重新調整中共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經過這次調整,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第二號人物的角色將由任弼時擔任,而剛剛在六屆四中全會擔任中央委員的留蘇派王稼祥則進入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構。[1-45]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委員會,研究富田事變的性質及處理意見。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三人委員會的意見,周恩來代表三人委員會發言:「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1-46] 會議決定:根據周恩來這一結論,由任弼時起草一信,要江西蘇區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處理富田事變,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起草的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于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于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1-47]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推翻了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決定,沉重地打擊了項英。 第一,否認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局)而剛剛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剝奪了項英在江西蘇區的最高領導權。 第二,明確規定,在中央代表團抵達之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享有指揮一切的最高權威,重新恢復了被取消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否認了1月中旬剛成立的項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合法性(事實上,1931年1月30日,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已決定重新組成由周恩來為書記的新的七人中央軍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組成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前往江西蘇區。作為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個高級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享有明確而全面的授權。為策安全,議定任弼時于3月5日出發,王稼祥3月7日啟程。 關于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至今沒有詳盡資料。1931年春,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機構是設在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系德國人,其人在共產國際地位較低,他的意見經常不被中共中央領導人重視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在「富農問題」等意見上的分歧,周恩來曾專程去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匯報。1931年夏秋,由于羅伯特向莫斯科匯報了李立三試圖把蘇聯拉入中國內戰的情報,以及遠東局對李立三的抵制,羅伯特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以至于共產國際專門派遣米夫秘密來華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據有關資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華後,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時間,但迄今也未發現有關米夫對富田事變發表看法的任何資料。 只有一兩份資料間接透露了有關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根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至于遠東局意見的具體內容如何,該書未作任何披露。但筆者根據周恩來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次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判斷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大概意見是:一、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二、不應夸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 筆者的這個判斷可從另一份資料中得到證實。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討論富田事變的政治局會議後,與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相異,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貿然肯定總前委反「AB團」的行動,因此在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沒有寫上總前委反AB團「一般是正確的」這句話。但是到了3月27日,遠東局改變了原有的看法,認定富田事變「是反革命的暴動,前委領導是對的」,甚至要求政治局與遠東局聯名發表對富田事變表態的決議。[1-48]這就是次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決議》究竟是誰起草的,迄今仍無直接資料予以證實,筆者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工負責蘇區與紅軍的工作,從1931年1月起,周恩來起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第一號通告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約七份有關涉及全黨政治路線、紅軍與蘇區工作,以及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信和電報。舉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來參與起草。《決議》體現了周恩來所特有的雖具強烈傾向性、但仍含折中色彩的思維及行事方式的風格,與周恩來在討論富田事變的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基本一致。《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斗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斗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決議》又說,「同時過分地估量反革命組織力量及它在群眾中的欺騙影響而減弱我們有群眾力量有正確路線可以戰勝階級敵人的堅強信心,這也是一種危險」。[1-49]1931年2月以後,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在對富田事變定性問題上一直持強硬態度,以任弼時為首的赴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忠實地執行了周恩來的方針,而根本不知道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等對富田事變的看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而具體改變肅反政策及糾正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則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後,此時,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幹部早已被冤殺。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帶著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經閩西到達贛南,和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會臺。在任弼時等未抵達江西蘇區之前的3月18日,項英曾主持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是項英為加強蘇區內部團結而開的一次會議,也是鞏固其在蘇區領導權威的一個重要行動。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剛剛收到的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的來信,具體討論的問題包括富田事變和「一、三軍團過去工作的檢閱」等。項英在談到蘇區中央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時,進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清楚認識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1-50] 然而,項英的意見在中央代表團抵達後立即被推翻。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下車伊始,馬上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六屆四中全會文件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意見,作為「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4月17日,由任弼時主持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項英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 《決議》批評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調和路線」下成立的,指責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完全是錯誤的」: (項英)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事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斗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由于推翻了項英對富田事變的分析和處理意見,中央代表團與毛澤東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關係。1931年5月,重新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澤東擔任書記。8月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通報由毛澤東正式取代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 項英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派別斗爭,工作能力不夠領導。因此喪失信仰,中央局決定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1-51] 與重新確立毛澤東領導權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審訊響應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開會的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在蘇區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長江局派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代表,隨後與毛澤東結成密切關係)為首的審判委員會,「首先把富田事變頭子劉敵執行槍決」,然後,依次「公審」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也一并處死。事隔三十年後,當年參加「公審」的曾山回憶了這次公審,他說: 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他們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而肯定是一個反毛團的組織。[1-52] 決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并不意味「肅AB團」運動已告「勝利完成」,相反,它標志著更大的「打AB團」風暴的襲來。1931年7月間,原在河西堅持游擊戰爭的紅二十軍在政委曾炳春和繼劉鐵超之後任軍長的蕭大鵬的說服教育下,服從中央局決定,回到蘇維埃中心區域的河東于都縣,但是等待他們的并不是歡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處決。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幹部,「士兵被分編到四軍、三軍團去」。被扣押的紅二十軍幹部,大部分被當作「AB團取消派」受到「處置」(即槍決)。 在地方,「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團分子」,「有的被錯誤處置,有的被監禁或停止工作」。[1-53]繼毛澤東在1930年發動「打AB團」運動後,江西蘇區的「肅AB團」只因項英的堅決制止才停頓了四個月,又在1931年4月後如火如荼全面開展起來,并在五、六、七三個月達到最高潮。 為了貫徹落實蘇區中央局4月17日《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提出的對「AB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的精神,加緊了對所謂「AB團」分子的刑訊逼供。「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對犯人普遍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所謂「軟」,「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1-54]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團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肅反機關則捕風捉影,「甚至于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1-55] 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1-56] 然而,在「肅AB團」的基礎上,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結成的友好合作關係,僅維持了七個月左右,一經解決了毛澤東與項英在「肅AB團」問題上的矛盾後,中央代表團和毛之間又逐漸產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個人權力與中央代表團權限的不明確,也加劇了雙方關係的緊張。至少在法理上,毛澤東是江西蘇區黨、軍隊、蘇維埃政權的最高領袖,而中央代表團的地位則不甚明確。從中共中央授權講,任弼時應是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但毛澤東已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因此,無論是從實力基礎或是從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法理權限講,毛已是蘇區最有權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團雖具權威,但只是處在一個監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蜜月終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結束,從此雙方開始了長達三年零兩個月的對抗和沖突。 注釋 [1-11]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伯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頁308。 [1-12]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頁307。 [1-13]《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76-77。 [1-14]《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1-15]《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34-35。 [1-16]《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646、648-49。 [1-17]《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26、631。 [1-18]《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110。 [1-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9。以下稱《毛澤東年譜》。另參見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90。 [1-20]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21]《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0—101 [1-22]《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23]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353;但據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告稱,李文林的父親只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閱《關于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查》,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1-24]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98。 [1-25]《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 [1-26]《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27]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1月14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未》,頁105-106。 [1-28]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頁107—108。 [1-29]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30]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1。 [1-31]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32]見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2。 [1-33]《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66。 [1-34]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35]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行,1985年);第14冊,頁634。 [1-36]《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85。 [1-37]《周恩來年譜》,頁183。 [1-38]《周恩來年譜》,頁185。 [1-39]《周恩來年譜》,頁192。 [1-40]《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1月16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頁639-42。 [1-41]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1-42]轉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1。 [1-43]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6。 [1-44]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484;另參見何盛明:《陳剛》,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4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84。 [1-45]《周恩來年譜》,頁203—204 [1-46]《周恩來年譜》,頁205。 [1-47]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141;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05。 [1-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9。 [1-49]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6;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08。 [1-50]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0年第6期。 [1-51]《蘇區中央局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1931年10月11日),轉引自《任弼時傳》,頁212。 [1-52]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斗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6月12日),載陳毅、蕭華等:《回憶中央蘇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1-23。 [1-53]《蕭克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1-54]《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1-55]《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77-78、480。 [1-56]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載中共中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三、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長時期以來,關于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斗爭的英雄。然而歷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 其實在肅反問題上,毛與中共中央并無原則上的分歧,雙方都一致肯定肅反的必要性,但是隨看周恩來等較深入地瞭解到蘇區肅反的真相,中共中央開始調整肅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糾偏的措施。同時,原先對毛個人專權的懷疑也在逐漸增長,中共中央加強了對毛的防范,并果斷中止了針對革命陣營內部的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行動。 1931年3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啟程赴贛後,中共中央在繼續強調富田事變「反革命性質」的同時,開始提及防止肅反「過火化」的問題。1931年7月下旬,隨任弼時等同赴江西蘇區的中央巡視員歐陽欽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蘇區存在大量「AB團」的論斷,并將此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1931年8月30日,周恩來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後,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蘇區「反AB團斗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在反「AB團」斗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余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1-57] 周恩來起草的這封信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被略去周的名字,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責。[1-58] 周恩來的這封信之所以使毛澤東不能忘懷,蓋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糾正「富農路線」的精神開始了對毛的不指名批評。 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在贛南會議上傳達了周恩來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時已深深地卷入到「肅A13團」運動,因此贛南會議把重點放在檢討土地政策方面,而沒有深入檢討肅反工作。雖然在贛南會議的《政治決議案》和1931年12月5日蘇區中央局致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都傳達了中共中央對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批評,并且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極有害的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的口號,但中央蘇區的亂打亂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AB團」運動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後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蘇區肅反與中共中央的「反右傾」路線及與蘇區領導層內部的斗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較為縝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與毛澤東發生直接的對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強了蘇區中央局的權威,才將中央蘇區從肅反大恐怖中解脫出來。 周恩來具體瞭解肅反所造成的慘禍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從閩西進入到贛南的途中。此時閩西正在轟轟烈烈開展一場與贛南「肅AB團」平行的肅反運動——「肅社民黨」,這場斗爭的殘酷性及對閩西蘇區造成的巨大破壞,促使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對蘇區肅反進行急剎車。 發生在閩西的「肅社會民主黨」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運動規模、肅反手段及殘酷程度方面,都與贛南的「肅AB團」難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時間裏,大批紅軍幹部、地方領導人及普通士兵、群眾被扣之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鎮壓,遇害者總數達6352人。[1-59]由此引發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伯翠脫離共產黨,擁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與富田事變類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變」。經這次肅反,閩西蘇區元氣大傷,黨員人數由原先的八千人,減至五千人。[1-60] 對于閩西的「肅社民黨」事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中央代表鄧發、閩西地方領導人張鼎丞、和中央代表團成員任弼時,各有其不同的責任。 受到共產國際「反右傾」路線影響,中共中央對待閩西「肅社民黨」的態度和對「肅AB團」完全一樣: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後,在繼續肯定「肅社民黨」的同時,重點轉向防止肅反的「過火化」、「簡單化」。 1931年4月4日,經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發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據國際路線和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全部的徹底的轉變」。[1-61]中共中央同日根據閩西給中央的報告,發出致閩粵贛特委信,對肅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積極的打入到黨的組織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閩西的所謂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從蔣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個的聯系和計劃的」,要求各級黨組織應對他們采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1-62] 中共中央的4月4日來信,對閩西的肅反起到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這封信究竟是誰起草的,大陸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據有關線索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管蘇區和軍事工作,凡涉及蘇區及軍事方面問題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來草擬,就在發出給閩粵贛特委信的當天,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發出。同日,周恩來還出席了討論湘鄂贛邊蘇區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會。作為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對閩西肅反的「過火化」、「擴大化」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 1931年夏,周恩來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認識發生明顯變化,在批評「肅AB團」問題上的「簡單化」、「擴大化」的同時,周恩來也對閩西的「肅社民黨」中暴露出的問題提出了較為直接的批評。 1931年9月中旬前後,由周恩來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送達閩西。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黨在閩西和其他地方是存在的」,又對閩西肅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 (社黨分子)既然能廣泛的深入我們的黨團和紅軍中去,經迭次破獲和逮捕以後,仍然時常發現他們在我們組織中活動?為什麽一部分被欺騙的群眾抱著觀望的態度不能自動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產黨?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從你們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最圓滿的回答。[1-63] 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的這種新態度,為他在抵達蘇區後對惡性肅反進行緊急糾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然而,在當時具有像周恩來這樣有靈活眼光的蘇區領導人少之又少,閩粵贛黨的最高負責人鄧發,就缺少周恩來的學養和眼光,他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 1930年12月,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選的中央委員鄧發到達閩西的龍巖,擔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從隸屬關係上,鄧發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于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閩西才與贛南蘇區打通,連成一片),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鄧發抵閩西後,即和當地幹部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全面負責起閩西蘇區的工作。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項英在前往贛西南的途中路經龍巖,曾與先期抵達的鄧發見面。項英抵達贛西南後,立即集中精力處理富田事變的後遺問題,未曾過問閩西的工作。 鄧發與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在中共早期歷史上,兩人都曾聲名顯赫。鄧發更因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擔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對「群眾專政」的一套較為熟悉。鄧發進入閩西蘇區後。一時頗看不慣在農村根據地中盛行的「流氓現象」和「流氓作風」,當鄧發看到蘇維埃文化部裏,竟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就憑直覺做出判斷,閩西黨和蘇維埃機關裏,已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當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戰員在大會上呼錯口號的事件發生後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于不瞭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復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鄧發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由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征,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入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 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開了閩西蘇區肅反大恐怖的帷幕,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系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1-64]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巖、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只有十六歲。[1-65]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閩西肅反的犧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黨員幹部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也反映了蘇區肅反運動的一個帶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沖的整肅對象。在1931年3月2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斗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1-66]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幹部和普通群眾陷入一片驚恐之中,許多幹部和戰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漂洋過海以求避難,更多的人則紛紛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區。 傅伯翠是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制度」受到閩西黨組織的批評,其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擔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後。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并派紅軍攻打傅的家鄉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幹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1-67] 1931年春夏之交,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在閩西政府所轄之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傅伯翠擁兵反抗之後,1931年5月27日,又爆發了在中共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的發生與被鎮壓,幾乎與贛西南的「富田事變」如出一轍。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坑口事變」消息,立即認定屬于「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作出決議,指示:「對于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1-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并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1-69] 鄧發作為中共閩西蘇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對于所發生的這一切極端行為,應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 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張鼎丞與充滿肅反狂熱的鄧發相比,其態度要相對溫和一些,但是他最終還是屈從于鄧發的意志。 張鼎丞是閩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創始者,極為熟悉閩西革命歷史和幹部狀況,是閩西地方幹部的代表人物。鄧發抵達閩西後,張鼎丞作為鄧發的副手,有責任向鄧發介紹他所瞭解的閩西幹部的真實情況,并在肅反襲來時盡全力保護幹部。但是迄今為止,這類事例還很少披露。相反,所能發現的,盡是以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的名義所發布的肅反通告。在這類文告中,尤以張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發布的「裁字」第一號、第二號給閩西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在發動「肅反」之初,張鼎丞曾在文告中規定,社黨主要負責人,應扣留嚴辦,一般成員在交代其行為後,令其自首,處以禁閉和警告。[1-70]閩西政府還曾公布《反動政治犯自首條例》,明文規定凡在半個月內自首者,不論其職務高低,概行免去處罰。然而,這些規定并沒有真正實行,隨著處決權迅速下放,這類政策條令形同一紙廢文。 1931年3月18日,閩西政府發出第二十五號通告,修改了處決人犯需報請閩西政府批準的規定。明確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先行刑,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1-71]這個新規定,造成大處決迅速蔓延,蘇區各級組織甚至包括醫院,都有權隨意逮捕、處決「社黨分子」。而在當時的狂熱氣氛下,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結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亂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隊、兒童團也多次破獲「社黨」。 自1931年3月處決權下放後,在近一年的時間裏,肅反成了閩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閩西政府要求各地在兩個月內肅清「社黨」。在上級號召的推動下,各級組織均以捕人愈多,處決愈快為革命最堅決的標準,一些對運動稍有懷疑的幹部,迅即被草率處決。永定縣委負責人謝獻球、盧肇西、曾牧村等因「對特委將社會民主黨名單要他拘捕,完全猶疑不堅決的態度」,而被冠之以「杜黨」罪名處死。[1-72]為自保性命,各機關實際上展開了一場殺「社黨」的大競賽。一旦開了殺戒,殺一人與殺一百人都一樣,肅反幹部的瘋狂與內心恐懼交織在一起,只有通過殺更多的「社黨」才能舒緩心理的失衡。于是,「肅反」野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來抵達閩西後才被撲滅。 張鼎丞對閩西肅反慘禍應負的另一份責任還在于他對主持肅反大計的林一株沒有發揮應有的約束力。林一株為閩西地方幹部,是閩粵贛特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閩西肅反中,擔任權勢極大的閩西政府肅反裁判部部長,是一個令無數人聞之色變的人物。有論著稱,林一株「在處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時,完全背著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1-73]這種說法有其一定的真實性,因為林一株直接聽命于鄧發,且有擅權之惡名。但是作為閩西黨的元老,張鼎丞應對本地幹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將閩西肅反慘禍的全部責任推到鄧發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張鼎丞與此毫無關係,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在閩西肅反中,張鼎丞始終處在安全和有權的地位。而在肅反高潮中,許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張鼎丞能對林一株發揮某種約束力。 在收到周恩來起草的批評閩西肅反擴大化的8月29日來信後,閩西最高領導對林一株的約束力立時就顯現出來。鄧發等把肅反干將林一株等拋出來,送上斷頭臺,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林一株在肅反傳送帶上終于走到了最後一站。9月29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九十七號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閩西「社黨」特委書記,同時指稱羅壽春(閩西政府秘書長)、張丹川(閩西政府文化部長)、熊炳華(閩西政府勞動監察部長)等八人為閩西「社黨」核心人員,分別予以處死。 張鼎丞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受到贛西南「肅AB團」的嚴重影響。這個時期,閩西與贛西南的交通雖未打通。但兩地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張鼎丞與毛澤東早在1929年就相識。率先在閩西打「社黨」的閩西地方部隊紅十二軍的主要領導人譚震林、羅炳輝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派來支持閩西的。在贛西南發起「肅AB團」,尤其在富田事變爆發後,張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動,繼而「頭腦發熱」應是不奇怪的。 對于閩西肅反慘禍,任弼時也有其間接的責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閩西肅反走向高潮之際,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在前往贛西南途中路經永定縣的虎崗,任弼時向鄧發等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要求閩西「集中火力反右傾」。閩西本來就左禍嚴重,如今又再「反右傾」,只能使左禍連天。任弼時在對待鄧發與項英的態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時在抵達贛西南後,不滿項英對肅反的消極態度,下令免去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而鄧發則繼續擔任閩西最高負責人的職務,這助長了本來就夠左的鄧發,使其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毛澤東與閩西肅反有無關聯,這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但從時間上判斷,項英進入贛西南後,毛澤東被免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毛并很快領導紅一方面軍與進攻蘇區的國民黨軍作戰,毛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肅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閩西肅反又是一件發生在贛西南眼皮底下、震動蘇區全局的事件,毛絕無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後,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批判項英,贛西南的「肅AB團」運動再掀高潮,而此時,閩西「打社黨」運動正方興未艾,此恰可證明開展「打AB團」的合理性。毛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場與「肅AB團」平行展開的「肅社黨」運動。 毛澤東深深卷入贛西南的「肅AB團」,沒有或較少涉入閩西「打社民黨」的事件,這些都決定了毛在對待這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 1931年9、10月後,周恩來起草的、包含有對「打AB團」過火化批評內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經傳到江西蘇區,毛開始受到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冷遇,毛逐漸調正自己的姿態,以擺脫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張鼎丞在瑞金參加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向毛匯報閩西肅反工作,毛指示張鼎丞,必須立即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并撥款五千銀元,作為善後救濟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漸削奪與周恩來關係較為密切的鄧發的權力,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又利用閩西肅反「擴大化」一案,進一步打擊鄧發。對于自己未曾直接卷入的閩西「肅社黨」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肅反之必要性,將其問題定性為「擴大化」。 鄧發作為此案的直接當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確表示,「今天來看,不僅當時全國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連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難說。」[1-74]然而毛澤東卻不愿直接承認閩西「肅社黨」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1-75]在這裏,毛澤東雖然提到了肅反的痛苦性,但沒有正面涉及為「打AB團」和「肅社黨」冤死者平反的問題,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個人責任問題。即使這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長期未予公布。 毛澤東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面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團」翻案,從而有損自己的聲譽。 1954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認為烈士。[1-76]但在根本問題上,即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否是冤案,則全部維持1931年的結論。直到1985年,在毛澤東去世九年後,這個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閩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閩西「肅社黨」運動不是什麽「擴大化」問題,而純屬歷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為閩西「社黨首領」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贛西南的「肅AB團」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隱去了毛澤東歷史責任後,才得到澄清。 毋庸置疑,周恩來對于蘇區肅反造成嚴重後果方面,應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是在肅反問題上,周與毛的態度有著顯著的差別。 種種跡象表明,周恩來是從推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理念出發而支持蘇區肅反,而無任何個人的動機;毛的行為則很難擺脫利用肅反剪滅異己的嫌疑。 周恩來正是因為從理念出發,當發生了贛西南「肅AB團」和富田事變後,在未深入瞭解實情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出中央指示信,客觀上助長了蘇區內已經蔓延的左禍。然而,毛則是極端的肅反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毛發動在前,周支持在後。 周恩來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點轉到糾正肅反擴大化方面,在進入中央蘇區後,用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才使瘋狂運轉的肅反機器停了下來,毛則鮮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因為蘇區肅反問題牽涉面廣。涉及到領導人的過失責任等敏感問題,周恩來小心翼翼,既要顯出糾偏的決心,又隨時作出妥協,盡最大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 1931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目睹了閩西肅反慘禍、從永定赴長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決議,制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周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目前問題已很嚴重,轉變非常困難」。周表示,自己決心「與此嚴重問題斗爭」。[1-77]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會讀通過《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1-78] 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與周意見一致的指示信,責令鄧發領導的省委必須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蘇區中央局還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閩粵贛省委和即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再次批評閩西「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并派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面軍的肅反冤案。在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來雖在肅反緊急剎車方面措施有力,但在處理有關責任人時,態度卻極為謹慎。1932年春,對閩西肅反慘禍負有直接責任的鄧發被調至瑞金,擔任權力極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一職。[1-79]任弼時則在周赴任後,出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周恩來。鄧發與任弼時的過失,也許被視為是「好心辦壞事」,因為對于這兩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肅反剪除異己的不良動機,因此與共產黨的黨道德和黨倫理并無沖突。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宜開展過分的黨內斗爭,這或許是周恩來對任命鄧發、任弼時新職的考慮。 至于毛澤東,問題則比較復雜。周恩來小心翼翼,不去觸及毛澤東,而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前閩粵贛省委)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周嚴厲批評了上述單位在肅反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1932年5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將毛澤東的老對頭、原贛西南黨和地方紅軍負責人李文林處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于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是造成贛西南肅反慘禍的禍首之一,[1-80]但只給予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極溫和的處分。周恩來主持的所有這類糾偏會議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評毛,對曾山、陳正人等基本上也沒有觸及。1932年初,因原先擔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患病,蘇區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繼續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老部下周興雖「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給其「留黨察看」的處分,[1-81]張鼎丞也在1932年3月後,繼續留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 盡管如此,周恩來實際上對于毛澤東已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以後又成為遷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來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錢壯飛還先後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 在被稱之為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的1932—1934這幾年,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承擔中央蘇區內部的肅反事務,不再由各機關、單位和軍隊自己大搞肅反。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1-82]但總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1-83]中央蘇區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一類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盡管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反」在1932年後已經基本停止,但是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內部仍然時斷時續地開展「反右傾」、「反托派」的斗爭,1932年6月後發生在瑞金的「工農劇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紅軍學校內的一些黨員知識分子發起組織了「工農劇社」,因在劇社章程中有「在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下,配合紅軍目前的偉大勝利」幾句話,很快被蘇區中央局指控為進行「托派」活動。8月13日,鄧穎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爭大會,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私貨」,因為所謂「社會主義」雲雲,就是否認了中國革命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全是托派的說法。鄧穎超還說,劇社章程沒提農民問題,這也是從托陳取消派的觀念出發的等等。在這天的斗爭會上,對工農劇社黨團會干事張愛萍等人開展了嚴厲的批斗。鄧穎超指責張愛萍「在反對反革命政治派別托陳取消派的斗爭中,他表現消沉不積極」,「非但未在黨的領導下,去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去深刻揭發并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在會後不久,⋯⋯對中央局將此事通知紅軍學校政治部表示不滿,⋯⋯企圖轉移斗爭的中心」。鄧穎超還指控張愛萍與「有重大嫌疑的人們(危拱之、王觀瀾)接近」,并說這是「他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1-84]在這次批斗會後,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給張愛萍書面嚴重警告處分,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的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1-85]所幸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時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們一定會因此而命喪黃泉。1932年後,中央蘇區的肅反已用較緩和的方式進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類似「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的大肅反運動仍繼續進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由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和由夏曦、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是兩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戰略根據地,「天高皇帝遠」,中共中央對兩地的領導必須通過張國燾、夏曦來實現。而此時的中央并沒有威權十足、足以號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張國燾也是具有某種梟雄氣質的領導人,一旦「肅反」成為其消滅異己、樹立自己權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會輕易放棄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進青年學生,全憑殺人樹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當夏曦嘗到肅反的甜頭,已猶如鴉片上癮,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讓其自行終止。 鄂豫皖(繼而在川陜根據地)、湘鄂西等地的惡性肅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終原因,是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立場。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肅反的前提下,提出「擴大化」及「糾偏」問題的,因而使張國燾等有機可乘。1932年10月後,張國燾率部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川北作大規模戰略轉移,中央對張國燾更是鞭長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也頻頻告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成為博古、周恩來等考慮的第一位問題,從而再難關注到對張國燾部及湘鄂西肅反的「糾偏」。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對蘇區肅反問題的復雜性和微妙性一無所知,卻從階級斗爭的理念出發,大談蘇區「肅AB團」斗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王明甚至認為1932年後中央肅反已不如過去那般堅決有力了,批評蘇區中央局「對于反對反革命組織及其活動的斗爭和警惕性有減弱的傾向」。[1-86]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這番話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只是現在形勢已大變。1932年後,毛澤東不再位居中央蘇區核心決策層,他已不需要為中央的政策承擔責任,而黨內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幾年後,毛澤東把這股情緒導引至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儼然自己一身清白。當毛將黨和軍隊大權牢牢掌握後,知情人紛紛三緘其口,最終,肅反問題反而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注釋 [1-57]《周恩來年譜》,頁212。 [1-58]參見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8-59。 [1-59]《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1-60]《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閩粵贛省委并轉省代表大會的信》(1932年2月1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96。 [1-61]《周恩來年譜》,頁209。 [1-62]《中央給閩粵贛特委的信——閩粵贛目前形勢和任務》(1931年4月4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3。 [1-63]《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49。 [1-64]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65]杭武縣蘇肅反委員會:《革命法庭》(1931年6月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66]《共青團閩西特委對肅清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決議》(1931年4月6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193。 [1-67]傅伯翠脫離中共後,曾接受國民黨委任的(上)杭、(龍)巖、連(城)邊界保安總隊隊長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後,傅伯翠曾接濟過在贛、粵、閩堅持游擊戰爭的共產黨游擊武裝。1949年5月,傅伯翠率所部三千余人歸順中共。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為傅伯翠平反,宣布其為「同志」,推翻傅身上的「社會民主黨領袖」的不實之詞。 [1-68]《中共閩粵贛省委關于杭武第三區事變決議》(1931年5月29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1-69]參見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7。 [1-70]《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號》(裁字第二號)(1931年2月21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8。 [1-71]《閩西蘇維埃政府通告第二十五號(裁字第四號)》(1931年3月18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1。 [1-72]參見《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1931年2月27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286。 [1-73]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94。 [1-74]《鄧發同志在閩西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2月23日)轉引自蔣伯英:《閩西革命根據地史》,頁189。 [1-7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干問題說明》(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121。 [1-76]《閩西「肅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6年第5期。 [1-77]伍豪自中區來信》(1931年12月18日),載《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76—77。 [1-7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18。 [1-79]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鄧發被任命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但正式組建機關是在周恩來抵達江西瑞金之後,時間約在1932年1至2月間。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建立的。 [1-80]1933年夏之前,李韶九曾被任命為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之後,李韶九被調往贛東北,擔任職務及最後結局不詳。 [1-81]《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481。 [1-82]《紅色中華》,1932年11月7日。 [1-83]李一氓:《模糊的熒屏——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59。 [1-84]鄧穎超:《火力向著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對它的腐朽的自由主義》,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5期,1932年10月25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69年),頁438—41。 [1-85]《中央局關于開除郭化玉危拱之羅欣然等黨籍與處分左權張愛萍同志的決議案》(1932年12月11日),載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編:《黨的建設》,第6期,1932年12月30日,轉引自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1931—1934)》,頁442。 [1-86]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64。 四、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諸多分歧中,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1至5日于瑞金召開的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不指名的批評了毛的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張,從而結束了中央代表團與毛長達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在1927—1931年幾經周折,發生過多次變化,其間毛曾一度制定過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還要激進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後適時作出調整,轉而采取較為務實的現實主義方針。但是,毛有關土地政策的思想演變過程十分復雜,即便在毛的思想發生轉變之後,他在對待富農問題上的態度仍然十分激進,極左的色彩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只強調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沖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與富農問題上曾持有的極左立場)。 標志毛澤東土地政策從較左的立場,轉向較具現實主義立場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親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實風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過左內容,明確宣布所有農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屬也可得到土地。後一條規定,是對共產國際有關主張的重大突破。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毛澤東在修正了共產國際某些極左方針的同時,又堅持了共產國際另一部分極左的方針,而與當時相對務實的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發生了沖突。 毛澤東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包括沒收農民土地;而中共六大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決定,則提出只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張沒收農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導致毛嚴厲鎮壓贛西南黨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贛西南方面堅持中共六大有關「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立場。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恰又與共產國際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提出《關于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案草案》,明確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農民的私有土地。毛澤東在土地與農民問題上的某些相對務實的主張,往往與更激進的極左主張相依相存。毛澤東對富農問題的看法,就具有這種特征。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并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方針。 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批評了違背農民意愿興辦「模范農場」的錯誤,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并無任何差別,甚至言辭更為激烈。 毛澤東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種土地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要像對「第一種」(「半地主性的」)、「第二種」(「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一樣,「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對于債務問題,僅僅四個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還規定,工農貧民之間的債務仍然有效,到了此時,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張,提出「廢除一切債務」的口號。毛并認為「廢除高利貸」的口號是錯誤的。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1-87] 對于毛澤東在富農問題上的極左主張,六屆四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贊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極左的方向急劇轉變。此時的中共中央已全盤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新路線,改變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據共產國際新制定的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決議,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時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讀案》,開始貫徹比毛更激進的土地政策。該決議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但隨即又將其貼上「非階級的」標簽。同時嚴厲批評給地主分田的方針「離開了土地革命的觀點」,宣布今後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只能分壞田。[1-88]同年8月30日,周恩來起草的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和沒有沒收富農的剩余農具)。[1-89] 接著,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按照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對毛澤東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評毛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隨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根據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 從1932年3月開始,在中央蘇區又展開了「土地檢查運動」,1933年,轉入查田運動。毛澤東雖被中央局責成領導這場運動,但毛因參與指揮戰爭,繼而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隨後長時間告假休養,直到1933年春毛才著手領導查田運動。 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的得力助手是王觀瀾。1931年王觀瀾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不久,被任命為《紅色中華》主編,但在1932年秋,王觀瀾被蘇區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紅色中華》主編職務,調到中央臨時政府,協助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毛派王觀瀾深入到葉坪鄉(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進行調查研究,為毛提供了許多生動具體的統計資料,把運動「搞得有聲有色」。[1-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權力的新形勢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有關「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采取了靈活的態度,他沒有公開反對這項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張也隨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蘇區中央局發表了毛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在以劃分階級成分為重點的查田運動全面推開後的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1-91]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雇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 然而毛澤東畢竟長期在農村戰斗,對農村狀況遠比博古、周恩來等人熟悉。在查田運動中,毛較多注意防止「過火」的傾向。由于運動遭到群眾的「冷淡」,中央局在不違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原則下,接受了毛的意見,對查田運動作局部調整。1933年10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頒布毛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由毛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開始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例如,勝利縣在毛的兩份文件下達後,就改正了錯劃地富共94戶。[1-92] 但是毛澤東對查田運動所作的調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轉,中央局懷疑毛的調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線。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訓令中字第一號」——《關于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其基本精神是「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借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訓令規定,「不論地主、富農提出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無效」,「地主、富農利用決定上的任何條文作為翻案的武器,必須防止。他們的一切反革命活動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制裁」。隨著這個訓令的貫徹,蘇區各地階級成分已經改正的農民紛紛又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勝利縣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分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1-93] 1934年2月以後的查田運動,隨著中央蘇區軍事形勢日益惡化。更趨極端。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地主一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于「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1-94]到了1934年7月,情況甚至發展到「造成一種削弱蘇維埃政權的無政府狀態」,以至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撰文號召「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1-95]但一切已為時晚矣。此時,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查田運動終告結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注釋 [1-87]《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1-88]《蘇區中央局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8月21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445、448。 [1-89]《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于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1931年8月30),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1),第7冊,頁361、357。 [1-90]參見蔡孝干:《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中共研究雜志社。1970年),頁103。 [1-91]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載《斗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92]王觀瀾:《繼續開展查田運動與無情的鎮壓地主富農的反攻》,載《紅色中華》,1934年3月20日。 [1-93]高自立:《繼續查田運動的初步檢查》,載《紅色中華》,1934年5月7日。 [1-94]《人民委員會為萬太群眾逃跑問題給萬太縣蘇主席團的指示信》,載《紅色中華》,1934年4月10日。 [1-95]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頁178—79。 五、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後,毛澤東迫于中共中央的壓力,被迫表示服從中央的路線,但是這種「服從」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優勢的軍事作戰領域,毛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見。 毛澤東不是軍人,但是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有關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在紅軍處于劣勢的條件下,毛的這些主張對保存、發展紅軍實力極為有用。但由于毛個性專斷「處事獨裁」,在用人方面有較強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時期內,毛在紅軍中的口碑遠低于作風民主的朱德。[1-96] 中共中央不滿于毛的軍事作戰方針始于贛南會議期間,在這次會議上,曾經提出過紅軍中存在著有待糾正的「狹隘經驗論」及「忽視陣地戰、白刃戰」的「游擊主義的傳統」的問題。[1-97]但是贛南會議的主題是批評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檢討蘇區的軍事戰略問題。中央代表團對毛的軍事方針的批評只是隱約其辭,任弼時、王稼祥等當時還是標準的文職黨幹部,讓他們去討論自己未曾經歷過的軍事作戰問題,顯然沒有像研討具有理論色彩的土地政策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軍事專家周恩來,及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幹部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後,中共中央與毛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漸顯現了出來,由攻打贛州而引發的有關軍事戰略問題上的激烈爭論,使毛與上海中央的沖突幾近白熱化。 攻打贛州的決策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932年1月9日,臨時政治局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號召「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斗」,同日,電令蘇區中央局「急攻贛州」。 周恩來對于是否執行攻打贛州的計劃,曾經有過數次變化。在未到蘇區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達贛南與毛交換意見後,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發電表示,在目前形勢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難。臨時政治局復電堅持原有意見,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發出訓令,決定攻打贛州。[1-98] 攻打贛州之役最後遭到失敗。1932年3月中旬,周恩來主持召開總結攻贛經驗教訓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集中兵力向北發展,打通贛東北的主張,但遭到否定。[1-99]會議采納了周恩來等多數人的意見,以贛江附近為中心,由彭德懷率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向贛江西岸出擊,爭取打通湘贛蘇區;由毛澤東率一、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向閩西發展。4月20日,毛率軍攻占了閩南重鎮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蘇區在軍事上的最大勝利。 漳洲戰役的勝利,暫時減緩了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不滿,但是隨著1932年6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和上海中央強令貫徹「進攻路線」,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圍繞軍事方針上的分歧重新尖銳起來,最終導致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四次圍剿改變了以往的戰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以掃清中央蘇區的外圍;繼而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為應付這種新的變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贛南會議上撤銷的紅一方面軍建制,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緊接著又仿蘇聯內戰體制,在人民委員會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席的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作為戰爭動員和指揮作戰名義上的最高機關。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趕赴前方與毛澤東會合,後方則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1-100] 此時的毛澤東正集中全力指揮戰事,但權責并不明確,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隨軍行動。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電中央局,建議以毛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其職權范圍為指揮作戰,行動方針的決定權則由周恩來掌握。對于周等的建議,中央局拒絕予以批準,堅持應由周擔任總政委一職。7月29日,周恩來致信中央局,再次堅持原有意見。周在信中說,如由他本人兼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使他改正錯誤」。[1-101]在周恩來的一再懇求下,中央局才照準周的提議,8月8日,任命毛為總政委。 毛澤東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就是一切以保存、壯大實力為前提,絕不與敵打消耗戰;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之薄弱環節,「與其傷敵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實際運用中,毛的這套作戰原則,經常表現為在敵進攻前,軍隊進行大幅度後退,這些又恰恰被臨時中央政治局視為是毛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等待主義」的集中體現。 1932年4月4日,張聞天(洛甫)發表著名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用「中央蘇區的同志」的代名,不點名地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1-102]4月11日,項英從江西秘密抵達上海,向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蘇區工作,幾個常委在發言中都對蘇區工作提出嚴厲批評。有的常委認為,中央蘇區領導在革命基本問題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觀點」,「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有的常委在發言中認為「狹隘經驗論」的實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1-103]正是在這種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瞭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斗」。[1-104] 毛澤東對于臨時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來信極不以為然,他在5月3日復電蘇區中央局,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是完全錯誤的」。[1-105]但是,周恩來對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聽計從,在收到中央來信後,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會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評,隨即宣稱,「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直接點名批評毛澤東,將其軍事主張定為「游擊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宣稱「澤東及其他純粹防御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 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1-107] 兩個月後,上海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及閩贛兩省委發出指示信。繼續批評中央局「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蘇區中央局「進行徹底的轉變」。[1-108] 面對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來不得不興兵作戰。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召開中央局會議,決定發動樂安、宜黃戰役,以威脅南昌,吸引圍剿鄂豫皖的國民黨軍隊。紅一方面軍攻占樂安、宜黃後,于8月24日進抵南城近郊,周、毛發現守敵強大,當即放棄攻城。從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軍分兵在贛江、撫河之間轉戰月余,這樣又受到中央局的嚴厲指責。 中央局堅持紅一方面軍應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軍應以「促起敵情變化」為方針,避免「急于求戰而遭不利」。[1-109]雙方電報往來十余次,互不相讓。9月29日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批評彼等的意見「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1-110]決定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即是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的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對毛澤東的指責十分激烈。會議對毛進行了面對面的批評,尤其指責毛「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上的錯誤」。雖然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評估攻打贛州以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但是問題最後都集中到批評毛對黨機關的態度上,毛的比較正確的軍事主張被會議否定,與此有密切關係。在1931年贛南會議後,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與毛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蘇區中央局利用軍事戰略問題的爭論,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布通令,調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與會絕大多數蘇區中央局成員的批評與指責,唯有周恩來的態度較為溫和,在一些問題上為毛澤東作了辯護和開脫。 對毛澤東批評最尖銳的是在後方瑞金主持蘇區中央局的代書記任弼時和中央局成員項英。任、項根據臨時中央2月以來有關加速反「右傾」的歷次決議,尤其依據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對蘇區中央局批評信的精神,尖銳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軍事方針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是「專等待敵人進攻」的保守的「等待觀念」。[1-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隨周恩來、毛澤東在前方指揮作戰,同屬四人最高軍事會議,客觀上也必須分擔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因此在寧都會議上并不積極,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時、項英等的看法。 周恩來作為前方四人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和前方負最後決定權的蘇區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反映了他一貫的作風和風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從維護黨、紅軍的愿望出發,對毛澤東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來在發言中承認在前方的最高軍事會議,「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認為後方中央局任弼時、項英等所強調的「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也批評後方同志對敵人大舉進攻認識不足,指出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周強調「澤東往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堅持毛澤東應留在前方。為此,周恩來提出兩種辦法供中央局選擇:「一種是由我負指揮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1-112]但與會「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上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後一種辦法。會議于是通過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辦法,并「批準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113]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周恩來卻因其在寧都會議上的折中態度受到蘇區中央局成員項英、顧作霖等的批評。1932年11月12日,後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其中涉及到對周恩來的看法:「恩來同志在會議前與前方其他同志意見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他(指周恩來——引者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瞭解此弱點加以克服」。[1-114] 同一日,周恩來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為自己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進行辯解:「我承認在會議上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的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會後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1-115] 根據現存資料,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并沒有接受蘇區中央局對他的指責,11月26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中央的電報中也稱,毛「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1-116]然而根據臨時中央11月給蘇區中央局的復電卻又看出,毛在壓力下,在會議上曾被迫作出承認「錯誤」的表態: 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同志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1-117] 毛澤東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犯下「錯誤」并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周恩來也是在肯定毛有錯誤的前提下,主張對毛采取較為寬和的態度,那麽繼續維護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蘇區中央局的團結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了。1932年11月,臨時中央復電蘇區中央局,指出:「恩來同志在(寧都)會議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18] 繼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來集中糾正毛的肅反偏差,現在又在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了毛的軍事作戰方針,毛在中央蘇區的權勢被一步步削奪。寧都會議結束後,蘇區中央局書記仍由周恩來擔任,當周在前方指揮作戰時,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則繼續由在後方的任弼時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達瑞金後,雖然局部調整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機構,但是寧都會議後形成的權力格局基本沒有變動。 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因在政治上蒙受打擊和患嚴重瘧疾,在長汀醫院休養達半年之久,周恩來曾數次請張聞天、博古勸毛回瑞金工作。[1-119]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瑞金,指示「要運用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瓦解敵軍和消耗敵人的戰術」,同時要求「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1-120]共產國際對毛的關照,對毛處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間毛返回瑞金,開始主管查田運動。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對一年前的寧都會議提出批評,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評擋了回去,重申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并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121]從此,毛未再予聞中央蘇區的軍事指揮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派代表前來蘇區聯絡商談雙方停戰之事時,毛才被允許參與某些重要軍事決策的討論。 根據1935年後的毛澤東的解釋,在關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軍的討論中,毛提議紅軍應向以江浙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出擊,以調動圍贛之敵,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同時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122]博古等人卻拒絕了毛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央蘇區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時陷于孤立,成為被迫長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的態度遠比上述解釋復雜的多。毛的有關紅軍出擊蘇浙皖贛的意見被否定,確實使打破「圍剿」失去了一個重要機會,但是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則肯定加劇了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危機。 福建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是堅決主張對陳銘樞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 至于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1-123] 如果說毛澤東的上述言論是在公眾場合依照中央路線而發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實想法,那麽在內部討論時,毛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據與毛關係一度十分密切、曾擔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回憶,在領導層討論陳銘樞、蔡廷鍇等人提出的要求與紅軍聯合行動的會議上,毛主張采取謹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的意見。[1-124] 龔楚的口述回憶只是提供了一種說法,是否完全確實,還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和證實。[1-125]由于毛澤東當時不處于核心決策層,即使毛反對援助陳銘樞、蔡廷鍇,這個決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作出。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導致與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實現,紅軍喪失最後機會,是由于共產國際及在滬的代表的錯誤指導,以及博古、周恩來的猶疑不決。 博古原是主張聯合蔡廷鍇的,并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博、周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實現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廣泛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1-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瑞金的中革軍委,催促早為決定紅三、五軍團是否參加側擊向福建前進的蔣介石入閩部隊。[1-127]周并經中央同意,派出潘漢年作為紅軍代表,與十九路軍談判并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博古、周恩來的意見,并沒有獲得中共核心層的一致支持,[1-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見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及駐華代表、中共上海局則起到決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產國際給瑞金來電,提出:「為著戰斗的行動的目的,應該爭取下層統一戰略的策略,國民黨的廣東派,以反日的武斷空話(護)符,隱蔽地為英帝國主義的奴仆,這種假象是應該揭穿的。」[1-129]這份電報對中共中央轉變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有重要影響。在滬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瑟・尤爾特、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他們一致認為,蔡廷鍇與蔣介石之間不過是軍閥間的一般斗爭,中央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斗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不給蔡廷鍇以實際的軍事援助。[1-130] 周恩來、博古等對于來自上海的意見并非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雙方曾互相爭論,電報往來不絕。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給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志發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對關門主義的左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產國際10月25日來電後,馬上轉變立場,在11月18日再次給福州黨的書記發了一封與前信內容完全相反的信,該信大罵十九路軍,聲稱他們與中共的停戰合作只是「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1-131]顯然,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周恩來、博古作了讓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見。[1-132]至于李德,據他稱,雖對他的頂頭上司弗雷德的計劃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認,他還是貫徹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決策層圍繞福建事變而發生的爭論中,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共對莫斯科的嚴重依賴和中共組織結構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達瑞金,與周恩來等會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幹部盛忠亮、李竹聲等也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從法理上講,在瑞金的中央局即應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活動,而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從上海向瑞金發指示電。周恩來在前線收到弗雷德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來的有關軍事作戰計劃的第一份電報,是在1933年4月14日。[1-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達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發出四份干預蘇區軍事行動計劃的電報。[1-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達上海,以後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之名而著稱。李德以後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過,似乎弗雷德更應為蘇區軍事失敗而負責,而回避了他自己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至于毛澤東,有關福建事變的爭論卻改善了他的處境。在這一時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處于有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蘇區軍事形勢日緊。毛的有關意見又逐漸被重視,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顯增強,這為他一年多後的復出埋下了伏筆。 注釋 [1-96]《龔楚將軍回憶錄》,頁207、357;另參見《黃克誠自述》,頁100—101。 [1-9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59。 [1-98]《周恩來年譜》,頁216-17。 [1-99]《彭德懷自述》,頁175-76;另見《周恩來年譜》,頁218。 [1-100]《周恩來年譜》,頁223。 [1-101]《周恩來年譜》,頁223-24。 [1-102]《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216。 [1-103]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290。 [1-104]《周恩來年譜》,頁219。 [1-105]《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79。 [1-106]《毛澤東年譜》,頁375;另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20。 [1-107]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最早收于1932年7月1日蘇區中央局出版的《為實現一省數省革命首先勝利與反機會主義的動搖而斗爭》小冊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的《六大以來》也收錄了此文,1991年復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沒有批評毛澤東的文字。據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開出版小冊子,此電文中有關涉及毛澤東的內容已被蘇區中央局所刪節,上述有關批評毛的電文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頁305。該書引用的這段電文沒有標明原始出處。 [1-108]《周恩來年譜》,頁223。 [1-109]《周恩來年譜》,頁228。 [1-110]《周恩來年譜》,頁230。 [1-111]《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12]《周恩來年譜》,頁231。 [1-11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2—1933,第8冊,頁530。 [1-114]《周恩來年譜》,頁233-34;另參見《任弼時傳》,頁245。 [1-115]《周恩來年譜》,頁233;另參見《任弼時傳》,頁244。 [1-116]《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1。 [1-117]《周恩來年譜》,頁234。 [1-118]《周恩來年譜》,頁234。 [1-119]《周恩來年譜》,頁245。 [1-120]《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33年3月),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398。 [1-121]《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03。 [1-122]參見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236。 [1-123]《紅色中華》,1934年8月1日。 [1-124]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64。關于龔楚和他的回憶錄《我與紅軍》一書的史料價值問題,楊尚昆在1984年7月9日的一次內部談話中曾說:「有一個叫龔楚的,在井岡山時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蘇區時是作戰處長。此人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被捕叛變,還帶敵人去抓陳毅。後來,龔楚寫了《我與紅軍》一書,在台灣、香港廣為流傳,書中寫了他是怎樣參加紅軍和在紅軍中做了些什麽工作。建國後我看了這本書,曾問過陳老總(指陳毅——引者注),他說龔楚的歷史就是那個樣子,叛變前的那一段歷史基本上是確實的。」見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84年7月9日),此講話稿經楊尚昆修訂,并征得楊本人同意後發表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 [1-125]龔楚在1978年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中修正了他在《我與紅軍》一書中有關蘇區核心層對福建事變爭論的敘述。龔楚稱他前書有誤,「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毛澤東被改為「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筆者認為,龔楚的更正應予以重視,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中的有關敘述,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故本書傾向于接受前一書的論斷,并認為此一問題的徹底澄清還有賴于新資料的發現。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513、515。 [1-126]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頁84、85;另參見龔楚:《我與紅軍》,頁364。 [1-127]《周恩來年譜》,頁254。 [1-128]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5。 [1-129]引自方長明:《試述共產國際與我黨對閩變的策略》,載《黨史資料與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1-130]參見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85—86。 [1-131]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事變檔案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20-21、133。 [1-132]據當時任中共駐十九路軍聯絡員張雲逸的回憶,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拉點隊伍過來」,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戰。參見張雲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載《福建事變檔案資料》,頁226。 [1-133]《周恩來年譜》,頁245。 [1-134]《周恩來年譜》,頁245-46、249-51。 六、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團舉行贛南會議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黨權大張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威得到完全確立和鞏固,沒有任何軍事閱歷、文職黨幹部出身的博古、張聞天等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老幹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澤東領導的軍隊。中央蘇區彌漫著「以俄為師」、全盤俄化的氣氛,而蘇區的創造者、黨與軍隊的元老毛澤東則備受壓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江西蘇區,中共中央迅速在組織上建立起黨對毛澤東的優勢。1931年春,繼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之後,大批幹部被陸續派往江西,其中許多人為留蘇返國幹部,計有劉伯承、葉劍英、朱瑞、楊尚昆、凱豐(何克全)、李伯釗、伍修權、肖勁光、劉伯堅等,林伯渠、董必武、聶榮臻、阮嘯仙等一批老幹部也在這一時期被調往江西,他們分別擔任了黨、軍、政、青等機構的領導職務。1933年1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抵達瑞金,在此前後,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羅邁(李維漢)、瞿秋白等也先後到達。博古、張聞天等到達後,和以周恩來為首的蘇區中央局會合,于1933年6月,組成了中共中央局,實際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蘇區順利地確立起領導權威,是與周恩來等的配合、協助分不開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來的力量舉足輕重,缺乏蘇區經驗的博古、張聞天等,離開周的支持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由于周恩來與留蘇派形成了實際上的聯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局中明顯處于劣勢。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與國際派的政治結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中央常委(書記處成員)中,國際派的博古、張聞天與老幹部派的周恩來、項英達成了權力平衡,毛澤東則未能進入這四人權力核心。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還進一步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基礎。毛所長期擔任的政府主席一職被分割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主席兩職。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職,幾乎成為一個虛職。 毛澤東之成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開始擔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中央執委會主席。在以後的幾年中,中央執委會下雖設立了人民委員會,但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毛基本上以中央執委會主席的名義行事。經中央局同意,毛陸續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鄧子恢、王觀瀾、[1-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內擔任人民委員或副人民委員,但是在博古等發動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職。毛的老部下張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蘇維埃主席,譚震林也被調離福建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工作崗位,毛成了一位「光桿司令」。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防范毛澤東在軍隊中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蘇區,在未抵達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級軍事幹部瞭解對朱、毛的看法。龔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雖具領導政治斗爭的才智和對軍事戰略的卓見,但其領導方式多有獨裁傾向。[1-136]博古到了瑞金後,為消除所謂「游擊主義」對紅軍的影響,指示周恩來等依照蘇聯紅軍的建制,對中央紅軍的作戰訓練、軍事教育開始了有系統的改造。過去,中革軍委主席一職雖長期由朱德擔任,但掌握軍隊實權的則是副主席周恩來。博古抵達瑞金後,周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後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達後,周的決策影響力進一步縮小,紅軍最高決策權又被轉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軍權,也許與周對毛的溫和態度有關。在周被削軍權的同時,對毛態度冷淡的項英被允許參與軍隊的決策,毛則完全被排斥于軍委之外,甚至連軍委委員也不是。在軍委總參謀部,正副總參謀長也分別由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與葉劍英擔任。劉、葉與毛在1931年以前幾乎沒有接觸,而與周恩來卻有較深的歷史淵源。 中共中央還利用自己在幹部上的優勢,在中央蘇區建立起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系統。在1931年以前,蘇區的所有宣傳鼓動工作全部在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統轄之下,毛享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解釋權。留蘇幹部進入蘇區後,出現瞭解釋權轉移的明顯趨勢。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後,國際派迅速在自己的強勢領域——宣傳解釋馬列方面行動起來,建立起一系列機構和學校。張聞天擔任了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1934年1月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黨校校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等職。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主編也從王觀瀾改由沙可夫擔任。國際派還創辦了《青年實話》、《蘇區反帝畫報》等一系列報刊。由國際派控制的黨刊,在配合對毛的影射攻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鄧、毛、謝、古」的斗爭中,中央局黨刊《斗爭》直接批判《毛澤覃同志的三國志熱》,明顯影射毛澤東。凡此種種,皆是觸發毛在幾年後攻讀馬列、繼而奪回解釋權的動因。 在共產國際的強大影響下,蘇聯之外的另一個蘇式社會在江西蘇區建成并初具規模。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直接脫胎于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斗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于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權限范圍完全類似于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裏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十七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彌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又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范學校、初級列寧師范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六十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裏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蘇區的形勢已極端危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毛澤東已被完全排擠出核心決策層,他「日夜憂思,對時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後,來到南線的于都視察,[1-137]在這裏他會見了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毛澤東對龔楚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毛竟凄然淚下![1-138] 所有這些表明,力圖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然而,博古等的成功僅是一種虛幻的假象,留蘇派最缺乏的是軍事方面的成功。在國民黨軍隊大舉圍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實質性的軍事勝利,其一切成功都猶如建筑在沙灘上的樓閣,一遇風浪,終將被摧毀。 注釋 [1-135]王觀瀾1931年自蘇聯返國進入中央蘇區,長期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工作,與毛私交其篤,毛稱其為「真正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參見趙來群:《毛澤東與王觀瀾》,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1-136]龔楚:《我與紅軍》(香港: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頁356—57。 [1-137]《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33。 [1-138]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頁550。 第二章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和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預 一、毛澤東逐步掌控軍權、黨權 毛澤東自詡為「以其道易天下者」,[2-1]「道」者,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也。那麽,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為一個已接受共產主義基本概念的中共領導人,致力于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面,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或許距毛當時所要實現的「道」不至相差太遠。然而,此「道」與被時一般共產黨人之「道」并無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時的毛已開始萌發若干有別于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片斷想法。毛基于多年在鄉村領導農民革命之體驗,已具體感受到在共產國際指揮下之中共中央諸多政策和實踐與中國社會環境之間存在嚴重沖突,而由此沖突顯示出的中國社會環境對莫斯科理論之拒斥,將嚴重阻礙中共在中國社會扎根、斷送中共取國民黨天下而代之的大業宏圖。 對于胸懷濟世之志,如毛澤東這樣的聰秀之人,「道」之產生并非太難,其乃源于對現實的直接感悟,只要將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難者,實現其「道」必先有其憑借,即所謂有道無恃,道乃虛空,有恃無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于一體,方可出現運動中的良性循環,并漸次向理想境界邁進。 如果說,1927年以前的毛澤東對上述三者之有機關係尚無直接感觸,那麽到了1935年,在歷經開創紅色根據地的萬般辛苦和多年黨內斗爭的沉浮後,毛對其間關係之體認就深鏤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澤東這個「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2-2]并被大家撿了起來,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義不容辭,在遵義會議後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極具現實感的毛澤東深知,在1935年,他實現其道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然而,遵義會議及以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人事變動,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第一次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離執掌黨和軍隊「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這種狀況雖非令毛滿意,但在當時,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毛選擇了「見好就收」的方針,主動放下黨內分歧,將全副精力用于對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維持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著并行的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并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麽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斗爭的戰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共軍隊的主要創造者之一,但是,毛對江西中央紅軍的實際控制力在1932年後的中共上層斗爭中逐漸被削弱,以至最終喪失。軍隊高級領導人受到黨的影響,對毛澤東漸趨疏遠,直至遵義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對軍隊的影響力仍是晦暗不明。將毛與軍隊領導人聯系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雙方對1934年後中共軍事指揮的不滿。因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獲勝後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其分散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重新聚合起來,將他在遵義會議上所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軍隊的掌握與控制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號稱十萬,實則八萬,自江西突圍,行至遵義時,因戰斗傷亡、脫隊,人數已減至三萬多人。領導這支軍隊的紅軍將領,分別是紅一軍團總指揮林彪和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而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和由賀龍、任弼時、蕭克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分別處于單獨作戰狀態,林、彭所率軍隊實際上是此時中共中央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林、彭也是毛澤東急欲駕馭的軍方兩個最重要的將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期改組中央機構階段,進入了中央常委會,但是紅軍的指揮權仍歸周恩來。毛澤東開始利用戰爭的緊急環境,有步驟地擴張自己在軍事指揮方面的影響力。1935年3月4日,在張聞天的提議下,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簽發命令,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2-3]這個建制與任命,雖然沒有改變周恩來的最後決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一職,是邁向掌握軍權的關鍵一步,但是幾天以後,圍繞是否攻打打鼓場,毛澤東的意見與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及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等發生了分歧。在3月10日由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剛擔任沒有幾天的前敵總指揮被撤消,由彭德懷暫代。[2-4] 在這決定毛澤東前途的關鍵時刻,毛毫不退縮,他于當晚找周恩來詳談,使周恩來接受了他不進攻打鼓場的主張。[2-5]緊接著,毛澤東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并得到了張聞天的贊成。[2-6]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在茍壩附近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成立「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批準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至此,毛澤東才正式進入軍委最高領導機構。 毛澤東在短短的一、兩天時間內,以堅強的意志力,挽回頹勢,更進一步擴大戰果,當仁不讓,毛遂自薦,提議組成有自己參加的新「三人團」,并通過黨的會議的形式,正式予以合法化,使自己名正言順地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決策者之一。 毛澤東進入新「三人團」後,迅速使自己處于核心決策的重要位置。在3月至5月的兩個月時間裏,毛澤東以大踏步回旋轉移的指揮戰略,集中中央紅軍在黔、滇、川之間穿插運動,其間,既有勝利,也有戰斗失利。頻繁的戰斗和就地打圈的戰略,使部隊疲憊不堪,更遭致紅軍高級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1935年5月上旬,由毛澤東部署的攻打會理城的戰斗,屢攻不下,這時紅軍領導層對毛的不滿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林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給周、毛、王「三人團」寫了一封信,提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2-7] 林彪的這封信是在中共及中央紅軍處于緊急狀態下寫出的,并無與毛澤東有意作對的念頭。在以往的歷史上,林彪與毛從無個人過節,林彪的這封信純系出自他對紅軍前途的考慮,表達的是當時紅軍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無獨有偶,類似林彪信中所反映的對毛澤東指揮才能的懷疑、不滿情緒在其他中共領導人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1935年4月中旬,劉少奇到紅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很快就感覺到部隊中彌漫著對「只走路不打仗」的強烈埋怨的情緒。他將瞭解到的軍中情緒,結合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發了一個電報,劉少奇拿著電報要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簽字,彭德懷認為電報所述內容與他的看法不同,拒絕簽字,楊尚昆則在電報上簽了字。[2-8] 在新「三人團」中,王稼祥與毛澤東關係較為密切,但是他對毛的指揮方法也存有疑竇。還在新「三人團」成立之前,王稼祥就常因作戰指揮問題,與毛發生爭論。王稼祥還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2-9]新「三人團」成立後,王稼祥對毛指揮部隊大幅度運動不以為然,他向張聞天表示,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2-10] 林彪的信和劉少奇的電報,對毛澤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這個事件性質之嚴重,不僅在于它顯示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已蔓延至當時中共中央所賴以依靠的唯一軍事力量——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而且這種不滿正向中央核心層蔓延,如不立即予以消除,毛剛剛獲得的軍權極有可能被再度削奪。 毛澤東迅速采取行動,正面反擊這股由林彪領頭的反毛風潮,他既不采取與林彪等私下溝通的方式,也不逐個向中央核心層成員解釋、征詢意見,而是將問題直接挑明。毛向張聞天建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得到了張聞天的同意。毛的目的非常清楚,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式,以黨的名義將對自己的不利輿論打壓下去。 1935年5月12日,旨在批評林彪等人「右傾」、「動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理郊外召開。與會者僅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及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這次會議名義上的主角是張聞天,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報告大綱,嚴厲指責林彪等人對毛軍事指揮的懷疑是右傾。在這個時刻。毛頗需要張聞天所擅長的理論語匯,只要將這股對自己不滿的風潮壓下去,扣什麽「帽子」都無所謂。 也許考慮到張聞天僅是一介書生,還不足以震懾林彪等武將,毛澤東全然不顧自己是當事人的身份,親自出馬。嚴厲指責林彪、劉少奇,稱彼等信和電報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2-11]毛并認定林彪是「娃娃」,不明事由,而將事先毫不知內情的彭德懷看成是幕後挑唆者。[2-12]毛在利用了張聞天作為反林彪、劉少奇的主攻手以後,迅速再將矛頭轉向張聞天。毛不能容忍張聞天扮演黨內最高仲裁者的角色,決意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一下張聞天的威信。毛在講話中暗指張聞天去三軍團,與彭德懷勾結反毛。[2-13]這次會議以肯定毛的軍事指揮、毛大獲全勝而結束。面對毛澤東的無端攻擊,彭德懷、張聞天抱著「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一切以大敵當前,內部宜安定為考慮,在會上和會後都未予以說明和解釋。[2-14] 會理會議對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地位的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說遵義會議意味著毛澤東獲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使毛進入了中共最高核心層,那麽會理會議則標志著毛已將他在政治上的勝利具體落實到對軍權的控制之上,從此,毛成為事實上的軍隊最高領導人。毛用其堅強的意志力,將紅軍最重要的將領林彪與彭德懷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使自己在核心層中處于不可批評的地位。毛澤東在會理會議前夕及會議上的行動,將剛剛獲得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置放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使代表黨的張聞天成為某種點縀和不具實際權威的象征人物。毛實際上用合法手段使自己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而這一切都是在周恩來對毛的妥協、退讓下實現的。 會理會議也給日後中共核心層的內部關係造成復雜影響,埋下了毛澤東對彭德懷、張聞天懷疑、猜忌的種子。毛與彭德懷共事很久,兩人個性殊異,雙方雖在1931年後關係疏遠,但是并無明顯矛盾和沖突。但是林彪信一事,使毛認定彭德懷城府很深,從此對彭深藏防忌之心。會理會議後,毛將曾參與劉少奇電報一事的楊尚昆調出三軍團,而改派自己的老故舊李富春任彭德懷的政委,實負監軍之責。毛對張聞天素無好感,僅是為了推翻博古,才使毛、張暫時聯合。毛對張的固有成見,使他在指責過劉少奇以後,將劉輕輕放過,并聽信了劉少奇對張聞天參與和彭勾結的猜測和判斷。劉與軍隊素無淵源,在軍中不具資望,毛并不認為劉少奇有在軍中掀風作浪的能力。劉少奇為脫身,迅速將責任推到張聞天身上,使剛剛開始的毛與張的政治結合蒙上了陰影,[2-15]也使毛對劉與張的對立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劉少奇電報一事,還是使毛多存一分心計,為避免劉少奇在軍中培植影響,會理會議以後,劉少奇也被調出三軍團。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陜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只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于中共黨內,人們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諳中國傳統兵法并將其靈活運用于開創中共根據地和發展中共武裝。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復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央政治局一班人迫于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脫離險境。而在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系起來,更遑論想象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即不再下來,并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占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看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三個系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系統置于自己的領導之下。擔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朱德、項英等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極大,但他并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并知會周恩來後,再發出作戰命令,盡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後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并入軍隊,全部權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3月,又根據毛的提議,重新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于「老三人團」,代表黨的張聞天并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2-16]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就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已溶為一體,當毛置身于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實際上他已處于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辟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軍隊的這種特殊關係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和其他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越來越處于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澤東對黨的大政方針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回,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一、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準)。但是,從莫斯科返國幹部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于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擴張黨權的第一個大動作出臺,由毛而非張聞天。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6年5月,由毛主見美國記者斯諾。 二、毛將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深情感聯系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2-17]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復,并劃歸于自己管轄之下。[2-18] 三、毛任命王首道取代鄧穎超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并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原國家政治保衛局機要系統,將原由鄧穎超負責的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于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2-19] 四、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末開始,毛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領導人插手,[2-20]從而確保自己在信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與便捷。 毛澤東對軍權與黨權的蠶食,是在張聞天的配合及利用了張聞天的黨的領袖地位,以公開的形式進行的,遵義會議後產生的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政治結合,為毛澤東擴張自己的權力提供了合法的掩護。 注釋 [2-1]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南寧:灕江出版社,1987年),頁319。 [2-2]《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南京:南京大學印行,無出版日期),頁4。 [2-3]《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0。 [2-4]張聞天:《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于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轉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2-5]《周恩來年譜》,頁277。 [2-6]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9。 [2-7]《彭德懷自述》,頁198。 [2-8]《彭德懷自述》,頁198。 [2-9]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18。 [2-10]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1。 [2-11]《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55。 [2-12]《彭德懷自述》,頁199。 [2-13]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引自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2。 [2-14]《彭德懷自述》,頁199;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23。 [2-15]毛澤東固執己見,認定張聞天在會理會議前夕唆使彭德懷、林彪反對自己,1941年後多次在核心層會議上就此事指責張。被毛無端指責的張聞天一直忍辱負重,不予辯白,直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再次提及此事時,張才在呈毛閱讀的《整風筆記》中作了自我辯解。張寫道,「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于此事有正式聲明)」。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233。張在此處提到的XXX同志極大可能是指劉少奇。從三十年代初開始,劉少奇就與張聞天長期處于對立狀態,有許多資料證明,劉少奇利用一切機會散布對張的不滿。1966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胡喬木揭發劉少奇在延安時曾在私下談話中影射攻擊毛澤東,劉少奇當即加以澄清,說自己當時只是針對張聞天,而非毛澤東。 [2-16]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2。 [2-17]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機關組成的陜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面軍番號恢復後,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頁293、306。 [2-18]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他工作人員均被并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只留下名義,工作權限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2-19]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陜北瓦案堡後,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恢復,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其實當時尚無中央社會部這個機構,此處所講的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實際上就是原國家政治保衛局管理的機要系統——筆者注),上述三個單位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費雲東、余貴華:《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921—1949)》(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6-87、204;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頁197。 [2-20]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45;另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03。 二、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建立在反對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及其後形成并逐漸得到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極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就加緊了與張聞天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誘導下,張聞天和王稼祥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張聞天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斗爭,讓張聞天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此舉使張聞天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張聞天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中共核心層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張聞天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盡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張聞天成為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至此,毛澤東與張聞天,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于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和張聞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鄉野打游擊,深受中國農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于高度自信的沉穩和持重,又帶有頗為濃厚的「山大王」氣息;而張則是「紅色教授」型的知識分子。1935年以前,張聞天對毛雖未予以高度重視,但亦無明顯的成見;然而,毛對張則有一種類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張等僅憑背了一麻袋馬列教條,卻在莫斯科支持下來蘇區奪權;毛更反感張以理論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報告問世,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毛和張雖在反對博古中央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戰略合作的關係,但毛從未將張放在眼裏。張聞天在軍中毫無基礎,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張聯盟中,張只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傾斜。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開始注意掩飾其個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觸及到利害關係,毛性格中的那種剛愎自用、猜忌防范心重的特征立時就暴露出來,毛在會理會議上的表現即是明顯的例證。 從毛這方面看,毛張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過與張聞天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占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張合作共事的幾年裏,對毛個性已有瞭解的張聞天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面沖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2-21]張聞天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于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面也與其個性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托的虛弱地位。張聞天乃一書生型領導人。置身于嚴酷的戰爭環境,只能唯毛馬首是瞻,盡管張聞天還堅持著最後一兩個陣地不愿輕易放棄。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大權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線方針方面,毛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黨內同僚的壓力下,他只能隱忍內心的不滿,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橫亙在毛澤東面前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也是毛澤東與張聞天政治結合的基礎。[2-22]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同時也出于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再繼續維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係到毛澤東能否實現其「道」,從而為黨及其個人在政治前途上開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張聞天。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幾乎本能地將自己的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系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張聞天的強烈反對。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著國內和平局面的到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舒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掌軍、張聞天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重大變化,張聞天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于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經過幾年的磨合,毛與周恩來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新的角色,張國燾在黨內斗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現在毛已十分具體地感受到張聞天給他帶來的困窘。對于毛而言,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繼續違心地接受令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于在條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于和張聞天及一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沖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張聞天發起挑戰。劉的出現打破了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并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意見的兩封信。劉少奇在這兩封各長達萬言的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于「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的極左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一、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左傾』錯誤」,[2-23]劉少奇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2-24]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二、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復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并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了中共有關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線。 三、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歷史,并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2-25] 劉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給張聞天寫信之前是否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派劉少奇為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陜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達。1937年2月,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未返陜北,[2-26]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陜北之間已建立了電臺和信使聯系。據1996年出版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別三次致電劉少奇,毛還在10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2-27]毛、劉通過電臺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2-28]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劉少奇給中央寫信都應被視為是一個重大舉動。劉少奇決定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黨內左傾分子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2-29]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政治權威。張聞天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盡管處于上升狀態,但當時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唯一領袖。[2-30]因此劉少奇給張聞天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歷史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志隨聲附合,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刷,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2-31]對于劉少奇有關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聲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并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當面向張聞天發起挑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後在毛澤東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從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重復3月4日給張聞天信中的精神,著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告激起強烈反響,張聞天、博古、凱豐、陳賡等都表示難以接受劉少奇的看法,認為劉少奇的批評,充滿托陳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共的論點。[2-32]柯慶施在發言中,更是指看劉少奇的鼻子罵他是「老右」。[2-33]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路線是正確的」。[2-34] 由于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會議暫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博古、凱豐在發言中都否認劉少奇提出的有關白區工作存在著一貫的左傾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傳統的說法,只有列席會議的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意見。[2-35]一時形勢對劉少奇明顯不利,然而毛澤東在關鍵時刻助了劉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劉張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贊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說劉系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言過的病癥,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甚至稱贊劉少奇「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中的辯證法」。[2-36]毛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只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後,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看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從而全面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張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2-37]由于毛澤東在發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張聞天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并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張聞天有意識淡化毛澤東在6月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2-38]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于什麽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斗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聞天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斗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斗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斗爭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張聞天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斗爭的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斗爭的價值」,把失敗的斗爭看成「無意義」或「謾罵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斗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義」。張聞天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成就,強調指出,「每一斗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于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夸大或縮小,或任便給同志們『戴大帽子』」。[2-39]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結論報告,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并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告作瞭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并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說到其他方面,并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2-40]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張聞天圍繞黨的十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并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到挫折。但是劉少奇、張聞天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于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影響絕非一朝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致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安排。 劉少奇與張聞天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張聞天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于劉少奇與張聞天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張聞天和黨內的巨大壓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并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愿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張聞天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張聞天。為了防止張聞天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張聞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并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離開中樞,但毛張聯盟從此走向解體,而毛、劉長達三十年政治結會的基礎卻因此爭論而告奠定。毛、劉與毛、張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張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張聞天有意忘卻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之間就圍繞此問題彼此交換過意見,并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張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2-41] 第二,毛澤東與張聞天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系。 第三,毛張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于毛和張聞天。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著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領導人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直線。就在毛澤東一路凱歌行進的1937年,也有壞消息傳來,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即將攜共產國際新方針返國,正待毛澤東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進行調整之際,半路上卻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毛澤東面臨著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注釋 [2-21]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32。毛澤東對洛甫的輕蔑態度在五十年代後期完全公開,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還不斷數落洛甫。 [2-22]張聞天在1943年整風期間寫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曾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2-23]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2。 [2-24]參見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載中固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 [2-25]參見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05-17。 [2-26]1937年3月4日,劉少奇致張聞天的信寫于北平,3月18日前劉仍在北平。周恩來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兩次致函劉少奇,并轉河北省委,要劉少奇等負起對留平、津地區的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58—59。 [2-27]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60、169、163。以下簡稱《劉少奇年譜》。 [2-28]劉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時握有與陜北聯絡的無線電密碼本。據當時擔任劉少奇譯電員的郭明秋回憶,她經手翻譯的劉少奇給陜北的電報,上款大都是洛甫(聞天)、恩來,「有時也直接接發給毛主席」,署名則是胡服(這是劉少奇在黨內長期使用的化名)。參見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載《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85。 [2-29]1936年3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天津,不久又擔任了北方局書記,著力糾正北方局「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劉少奇領導的糾偏工作,除了思想糾偏之外,還包括糾北方局領導機構的改組,因而引起北方局內部的爭論。劉少奇上任後,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與劉同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取代柯慶施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任命陳伯達為宣傅部長。劉的這些措施激起柯慶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領導人的不滿,劉在黨內頻頻發表文章,不指名批評柯慶施等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從而埋下柯慶施與劉少奇長期不和的種子。 [2-30]劉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給張聞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澤東,劉且寫道:「我國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817。由此可見,安時毛的權威并未得到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一致承認。 [2-3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75。 [2-32]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1年),頁189;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58—59。 [2-33]楊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懷念少奇同志》一文中,雖末點出柯慶施名。但他所稱的「那個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明齟指柯慶施。參見《緬懷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5。 [2-34]出席白區工作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及廣東代表約三十人。彭真作為華北代表團團長,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的助手。華北代表團的代表有柯慶施、高文華(原河北省委書記,兼原北方局書記職能)、吳德、李昌、李雪峰、黎玉、烏蘭夫等。據參加過這次會議、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黎玉回憶,劉少奇的報告「對『左』的錯誤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關「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的說法「有點過頭」,因為參加會議的「北方黨組織的代表這麽多,就說明白區的損失不能說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當時參加會議部分代表的觀點。參見黎玉:《抗戰前夕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代表會議》,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2—43;另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95。 [2-35]中共山西省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8。 [2-36]《劉少奇傳》,上,頁26。 [2-37]《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另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72。 [2-38]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71。 [2-39]張聞天:《白區黨目前中心任務》(1937年6月6日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告之一部分),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234-36、238-39、261、263。 [2-40]參見陳紹疇:《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頁298;另參見《劉少奇年譜》,上卷,頁183。 [2-41]據1931年秋至1932年底與劉少奇同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一度與劉少奇夫婦同住的張瓊的回憶,劉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區工作的策略問題寫信給毛澤東,批評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不久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來一封很長的回信」,表示贊成劉少奇提出的穩健主張。參見張瓊:《劉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載《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8、47。 三、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逐步控制了中共軍隊,并大大加強了他對中央機關的影響力,但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尚未能將他的勢力延伸到中共領導機構的另一組成部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優勢,在中共黨內獲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將不得不與從未謀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團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1931年11月7日抵達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達的康生(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和1935年8月抵達的陳雲(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工人出身的陳郁雖是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員,但陳郁因在1930年未一度參與羅章龍派的活動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罰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并不參加代表團的實際工作。除了這四名政治局委員,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吳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饒漱石、趙毅敏,和1933—1935年赴蘇的中國蘇區代表團成員高自立、滕代遠、白區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團成員同時還兼任中國各赤色組織駐莫斯科的代表,黃藥眠、饒漱石先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林毓英任中國赤色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中了中共在蘇區以外最龐大的領導陣容。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在蘇聯期間,正是國內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向江西蘇區轉移、共產國際蘊釀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方針的時期,保持與國內聯系信道的暢通成為代表團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中共代表團通過兩個渠道與國內的中共中央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一、開通大功率無線電秘密電臺、中共代表團通過共產國際的電臺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電臺,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地下電臺保持經常的秘密聯系。因距離遙遠和技術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與江西瑞金沒有直接的電訊聯系,而必須通過在上海的秘密電台中轉。遠東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遷江西後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別有自己的秘密電臺,遠東局給瑞金的電報須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電臺翻譯轉送。代表團與國內的電訊聯系在紅軍長征後中斷。1935年末林毓英攜密碼本自蘇聯秘密返回陜北,國內與莫斯科的電訊初步恢復,而當1936年劉長勝再攜密碼本回到陜北後,在陜北的中共中央與代表團的電訊聯系就得到完全恢復。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團通過回國的中共黨員向國內的領導機構傳遞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開赴蘇訪問的著名新聞記者、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就曾為中共中央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傳遞情報。共產國際并借助在中國國內的中共組織的協助,招募中共黨員為其搜集情報,這些直屬莫斯科指揮的中共黨員,間或也為莫斯科與上海的中共中央傳遞消息。[2-42] 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代表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向中共傳達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起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代表團的另一項工作職責是領導在蘇聯學習、工作的中共黨員。從1931年11月王明赴蘇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面: 一、在共產國際內展開對中共及中國工農紅軍的大規模宣傳。王明自抵蘇聯後,以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經常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文章,宣傳中共主張,介紹蘇區各方面情況。1932年王明指派蕭三以詩人身份參加在蘇聯哈爾科夫召開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大會,與高爾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聯絡,以擴大中共的影響。1935年,王明又指派吳玉章、饒漱石等前往巴黎,創辦中共報紙《救國報》(後易名為《救國時報》)。王明并以其在共產國際分工主管拉美共產黨事務的便利,指導美國共產黨內的中共支部,在美國創辦華文報刊。 二、領導在蘇聯的中共黨員。三十年代在蘇聯仍有不少中共黨員,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和莫斯科的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等單位。在遠東地區也有一批中共黨員在蘇聯各單位工作。由于在蘇聯的許多中共黨員同時又是蘇共黨員,中共代表團所能領導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黨員,莫斯科以外的黨員基本上歸蘇共領導。 三、配合蘇共清黨,在莫斯科中共黨員中厲行肅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曾密切配合校長米夫和蘇聯秘密警察「格伯烏」,將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學生投入監獄,或送至西伯利亞和北極地區勞改。[2-43]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開始大規模鎮壓在蘇華人,莫斯科華僑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處死,「新經濟政策」後一度興起的華人商業繁榮的局面頓時消失殆盡,中國人在蘇聯的處境日益艱難。[2-44]遠東地區的鎮壓則更為殘酷,許多進入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游擊隊員被當作「日本間諜」投放到勞改營。[2-45]1934年後,蘇聯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黨運動,王明、康生緊緊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內也展開類似運動,代表團成員楊之華(瞿秋白之妻)、曾涌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擊。[2-46] 四、援救西路軍。1937年初,中共代表團爭取到共產國際的大量軍火援助,以接濟準備進入新疆的西路軍。計有五萬支步槍,上百挺輕重機槍和幾十門大炮。陳雲、滕代遠、馮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圖,等待西路軍的訊息,後因西路軍失敗,此事告吹。[2-47] 中共代表團除了上述四個方面的工作以外,還有一項特別的工作,這就是指導中共滿洲省委。1932年後,因日本侵占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已無法與上海中央局正常聯絡,轉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王明等曾多次發出給滿洲省委的指示信,并派人潛入東北。滿洲省委和抗聯也多次派人去蘇聯向代表團匯報工作。 中共代表團領導滿洲省委是特殊形勢下的一個例外——滿洲省委與莫斯科的聯絡遠比與上海的聯絡更便捷。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無權干預中共國內的事務,但是在事實上,以王明為團長的代表團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對國內領導層的影響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對國內的影響主要源之于他的共產國際背景和當時他在國內項導層中所擁有的政治優勢。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來的中共領導人。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強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指定為政治局委員,緊接著王明赴蘇,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便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東方部副部長、部長,因而被公認是「國際路線」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產國際的化身,王明所擁有的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可以隨時向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表述其個人的意見。 王明在國內有一批盟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線」的英雄,與王明一道進入中共領導層,稍後返國的張聞天在政治上也屬于王明、博古集團。在王明赴蘇後,博古等人都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與王明的關係是一種「聲氣相求」、「共存共榮」的政治盟友關係。由莫斯科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之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成為王明、博古等領導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據。王明作為六屆四中全會上臺的一批人的精神領袖,對在國內的博古等人無可置疑地具有影響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對國內的中共中央實行遙控?從現在已披露的歷史資料看,王明和代表團一般不對國內的具體活動進行直接干預,但是在某些時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問題向江西表達自己的意見。在1931至1935年,王明與國內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導致王明與國內產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產國際即將開始新的策略方針從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但是,國內的博古等人仍堅持舊有路線,拒不同意調整方針。 王明在莫斯科對他在國內的盟友一直持堅定的支持態度,對毛澤東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多有貶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產國際的講壇上高度稱贊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總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發言,他宣稱: 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執委這個全會上,完全有權利高興地向一切兄弟黨說:我們黨在其布爾塞維克中央領導之下,現在達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歷史當中空前未有過的統一,團結和一致。[2-48] 與王明對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據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陳修良等人回憶,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過「山溝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2-49]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主持召開「寧都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毛的軍事主張也被指責為「右傾」和「保守主義」。會議後,在上海的博古、張聞天迅速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王明很快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對博古等作出呼應。他用幾乎與博古、張聞天完全一樣的語言,指責「黨內一部分分子,對于國民黨軍事圍剿和日漸逼近的帝國主義對蘇維埃革命的公開武裝干涉表示悲觀、失望和消極的情緒和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黨在中央的領導之下」,對「目前階段的主要危險——右傾傾向」進行斗爭。[2-50] 王明與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漸發生變化,王明開始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同意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 1932年3月,王明發表文章,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責國內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眾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面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王明還指出「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2-51] 1933年1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采取的全面沒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王明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觀點,制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2-52] 博古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見完全置之不理,與一般人所想象的情況絕然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對王明亦步亦趨。此時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蘇區第一號人物的地位,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博古更加堅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來博古的立場在蘇區內部就已受到張聞天的質疑,[2-53]現在連王明也提出批評,但是,博古對所有這類批評都采取了堅決「擋回去」的態度。博古的僵硬立場引致王明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個時刻,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也從冷淡轉向熱烈。 王明對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大致以1934年為界。在這前幾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對毛澤東的「批評」、「幫助」。王明自認為在黨內的基礎鞏固,對毛澤東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面認識,也還沒有將毛視為是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在這個階段,王明對毛澤東輕視、忽略有之,但認為王明出于防范毛澤東的個人動機,在莫斯科處心積慮貶損毛,則未免言過其實,也缺乏事實依據。1934年後,隨著王明對博古不滿的加深,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明開始在共產國際的講臺上宣傳毛對中共的貢獻。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試圖返回國內進入中央蘇區,但最終因知曉王明返國計劃的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2-54]為了修補因長期脫離國內艱苦斗爭而對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損害,在毛澤東已受到黨內批評、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王明向毛澤東援之以手,不僅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在黨內核心層中的影響,更可使自己在黨內矛盾中處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從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陸續做出一些姿態,試圖建立起和毛澤東較為親善的關係。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在蘇區發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對于缺點和錯誤的過分和夸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沒有一個白區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領導之下的群眾團體的黨團,不被指出過(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嚴重的或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兩面派的錯誤,⋯⋯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分和夸大的批評,既不合適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B、對于黨內斗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志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于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2-55] 王明、康生雖然沒有完全否定「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但是這封信還是使已進行一年的「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停了下來。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當年1月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讀案》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存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2-56]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對博古的這類批評,不僅未被承認,反而將其定為是王明的主張,王明當年對政治局的批評意見,幾乎被毛澤東全盤接受下來,只是已被當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轉移前來自遠方的最後一次信息。王明在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準備召開七大以及對西北問題的指示後,專門談及共產國際出版毛澤東文集的事宜: 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指毛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志三篇文章(我們這裏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有極大的作用。[2-57] 隨後,在中共代表團的協助下,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收有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等文件,并譯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發行。這樣,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人能夠有資格在蘇聯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澤東。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來信後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及八萬六千名紅軍開始撤離中央蘇區。對于這一決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蘇區軍事戰略重鎮廣昌被國民黨軍攻占後,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將主力撤離江西,進行戰略轉移,并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2-58]在共產國際復電批準轉移計劃後,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負責戰略轉移的全部準備工作。從1934年10月上旬紅軍長征開始,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已中斷。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過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1月14日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開始長征。 王明在這種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他對國內中共中央的批評。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六次戰爭與紅軍戰略)的報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因為紅軍已開始長征,未能傳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報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國內形勢「新特點」的錯誤,尤其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誤和弱點」。王明還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宣稱由于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從而加劇了紅軍沖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在中央紅軍撤出江西蘇區的背景下,王明對中共中央的這些批評,與已經形成的嚴重危機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他與博古等在一系列問題上分歧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一段時間內,王明并不知曉(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陳雲一行抵達莫斯科後,才獲知有關遵義會議的詳情的),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復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2-59]此時的王明并不知道博古已經下臺、毛澤東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繼續在一些重大場合中向毛澤東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于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例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將他們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2-60] 縱觀王明在1931—1935年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態度變化的過程,可以發現,王明對毛澤東看法的轉變是與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漸擴大互相聯緊的。1932年後,王明受到共產國際調整政策的影響,其原有的極左思想發生明顯變化,而在國內的博古因消息閉塞,兼之頭腦僵化,卻繼續恪守共產國際舊時的政策。王明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對黨內高層關係的復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于是改善并加強與國內毛澤東的關係,就成了1934年後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動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黨內所處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準備,和毛澤東等其他領導人攜手合作。 注釋 [2-42]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蘇聯著名間諜佐爾格主持,1932—1933年佐爾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動,佐爾格去日本後,遠東情報局由華爾敦主持。遠東情報局于1935年春被國民黨破獲。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頁279;另見于生:《轟動一時的神秘「西人案」》,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156—64。 [2-43]參見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載《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載《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關反映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流放、勞改的資料有馬員生的《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2-44]莫斯科廣播電臺,1993年1月3日23:20華語廣播。 [2-45]參見姚艮:《一個朝圣者的囚徒經歷》(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315。 [2-46]參見孔原:《懷念敬愛的稼祥同志》,載《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8;另見蹇先任:《38年留蘇紀事》,載《革命史資料》,第1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39。 [2-47]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42—43。 [2-48]參見王明:《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12。 [2-49]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斗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頁56。 [2-50]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2-51]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2-52]王明:《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2—23。 [2-53]程中原:《張聞天傳》,頁168-70。 [2-54]據1934至19SS年擔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盛岳(盛忠亮)回憶,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產國際多次來電,要求為王明進入中央蘇區加緊準備香港——汕頭——閩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為此曾兩次派人前往香港進行布置,但最終因上海地下電臺臺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參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杜,1980年),頁269。 [2-5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26—17。 [2-56]《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55—57。 [2-57]《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84。 [2-58]《周恩來年譜》,頁262。 [2-59]參見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15。 [2-60]參見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8月7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449。1937年王明返國後,對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的中共領導人中,刪去了張國燾的名字,增補了董必武、徐特立兩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參見《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 四、在「反蔣抗日」問題上毛澤東與莫斯科的分歧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奉命離開正在長征中的中央紅軍,于5月輾轉到達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後,陳雲與已在上海的陳潭秋、楊之華、何實山等會合,作為中共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經由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秘密安排,在滬搭乘蘇聯貨輪,前往海參崴,于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日的8月20日到達莫斯科。在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駐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幹部,前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化名陳剛也抵達莫斯科。從陳雲那裏,王明第一次瞭解到有關長征和遵義會議的全部詳情。從此,在王明與毛澤東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錯綜復雜的關係。 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圍繞統一戰線問題產生的意見分歧,始終占據突出的位置,成為日後毛、王公開沖突的導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奉行共產國際的關門主義政策,號召建立下層統一戰線,「武裝擁護蘇聯」王明對此政策的推行負有完全的責任。從1931年11月王明抵蘇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這項政策,但是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進而成為中共領導層中倡議轉變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這次會議鑒于歐、亞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嚴重形勢,開始修正過去的一些僵硬的觀點,認為存在著爭取社會民主黨下層群眾、建立工人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王明受到這次會議的啟發,逐步醞釀在中國也調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起草了著名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明確宣布,中共愿與國民黨外的一切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政治黨派進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給中共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史稱「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東北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年春,王明還參與指導國內的中共組織與馮玉祥的聯絡活動。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應關注「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并隨信附上他們起草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內戰」的文件,經宋慶齡等1779人簽名,于1934年4月20日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到了1934年春共產國際預備召開七大期間,王明思想轉變的步伐進一步加快。該年春,共產國際加緊醞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的這一新動向,對王明產生了重要影響。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關門主義、改變打擊中間階層的過左政策的主張。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條件與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年10月,王明在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廣泛協商討論後,起草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發表,把統一戰線的范圍擴大到除蔣介石以外的國內一切黨派,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而到了該年底,王明在《救國時報》撰文,宣傳「聯蔣抗日」,將蔣介石也納入到統一戰線的范圍。 然而,根據現有的資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對于王明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由于國內反應冷淡,王明還托從莫斯科返國的同志向國內領導機關傳達口頭信息。 1933年秋,王明與即將返國的中國共青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談話。王明說,中共應在戰略上實行轉變,逼迫蔣介石抗日。王明又說,國民黨雖是我們的敵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敵人,由于日本已損害了國民黨的利益,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英美派利益,國民黨中下層,甚至高級軍官都可能贊成統一戰線。王明進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開局面,就是因為黨的政綱與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眾的掩護和支持。[2-61] 王明的這番談話給黃藥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此時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觀點與王明并不一致。當黃藥眠向米夫辭行時,米夫要他轉告國內「還是照舊的方針領導」。[2-62]黃藥眠返回上海後,迅速把王明的意見轉告給當時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人黃文杰,上海局又通過地下電臺將此意見向江西蘇區作了傳達,[2-63]但是王明的建議如同石沉大海,沒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領導人的任何響應。 由此可見,從1933年初開始,隨著共產國際醞釀策略轉變,王明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聯系中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形勢,為中共設計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有別于舊時以國共兩黨斗爭為主題的路線,其核心是,共產黨在國內階級關係發生新變化的形勢下,應加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應改變過去的關門主義和一系列過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并在這場運動中發展壯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來自于共產國際,另一方面,也有他個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產國際遠一些,這也是國內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王明在莫斯科頻頻談論統一戰線問題時,遠在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正處于沒有發言權的地位,故而未見毛澤東有任何談論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述。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後,面對紅軍嚴重被削弱及國內的新形勢,毛澤東正急謀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時,張浩(林毓英)化裝潛入陜北,帶來共產國際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與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的召開。然而,毛、王雖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人的側重點卻大相逕庭,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考極具現實主義色彩,而王明則對之過于理想化。 毛澤東迅速接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但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利用統一戰線,首先緩解陜北的剿共危機,解決紅軍和共產黨的生存問題,繼而謀求共產黨和紅軍的更大發展。在瓦窯堡會議後,毛決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進攻陜北蘇區的東北軍、西北軍的白軍工作委員會,以謀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成效。 王明在萬裏之遙的莫斯科,則遠比毛澤東「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陜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統一戰線的重點放在爭取全國范圍內實現國共合作抗日,頭號爭取對象就是蔣介石。1935年8月20日,陳雲抵達莫斯科後,王明才真正瞭解到紅軍的實力已大大受挫,緊接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于8月25至27日連續召開會議,決定把反蔣抗日統一戰線,改為聯蔣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不斷刊文,呼吁國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國時報》連載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正式提出「逼蔣抗日」的主張。只是當傳來蔣介石在1935年12月鎮壓北京學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後,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蔣抗日」的口號。 毛澤東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差異自1936年後逐漸顯現出來。毛澤東力主利用一切反蔣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則強調支持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領袖,堅決反對各地方派的反蔣活動。1936年下半年,圍繞「兩廣事變」,毛澤東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終于爆發。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以「反蔣抗日」為由,發動「兩廣事變」,中共聞之消息,立即表示支持,稱其具有「進步的與革命的性質」。[2-64]6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提出以中共為中心,與西南建立抗日聯軍的主張,并且強調「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與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2-65]與此同時,毛澤東積極推動與包圍陜北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談判,6月,中共方面已與張學良、楊虎城部簽訂了停戰秘密協定。然而,中共聯絡西南的活動并不順利,西南方面拒絕了中共的建議。7月,兩廣方面與蔣介石妥協,事變得到平息。盡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獲,毛澤東不費一兵一卒,解決了陜北的生存危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幫助毛澤東做成了這筆「無本生意」。 但是,毛澤東的上述活動卻遭到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責。兩廣事變爆發後,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發表社論,譴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起中國內戰,以便利于掩蓋對華北新的進攻」的一場陰謀。[2-66]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發表批評中共的講話,他說,「不能說,在政治方面,在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這種復雜的情勢下,他們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領導人——引者注)和做好了準備」。季氏強調將抗日與反蔣并舉是「錯誤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聯合反蔣也是「錯誤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蔣抗日」的方針,并給國民黨發出公開信,表示自己愿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立場。季氏重申,中國現階段一切均應服從反日斗爭,他并建議中共以「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代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口號。[2-67] 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的指責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轉含蓄地批評國內同志恪守過時的反蔣抗日的政策,王明問道:「為什麽中共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2-68] 這場圍繞兩廣事變而引發的「反蔣抗日」問題的爭論,以毛澤東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見而告結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的公開信,倡議建立國共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通知,決定采用「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以「民主共和國」代替「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 這是毛澤東主政中共後第一次與莫斯科打交道,它給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從此,毛澤東有了自己對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這就是對「遠方」的指示,適合口味的就辦,不適合口味的就拖延不辦;如果「遠方」的壓力太大,則采取偷梁換柱的方法,對其做過加工後再執行。總之,務求莫斯科的指示與中共的發展不致有太大的沖突,更不能與加強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相沖突。毛澤東最後接受「逼蔣抗日」的方針及和平處理西安事變,[2-69]就是依據了這種策略。結果,莫斯科雖對毛澤東陽奉陰違不滿,但都因毛澤東最後還是貫徹了「遠方」的意圖而原諒了毛。 毛澤東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對季米特洛夫無可奈何,但是,對王明則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澤東對王明雖無好感,但兩人并沒有直接打過交道,與毛交惡的是博古、張聞天等人。現在王明跟著季米特洛夫的後面鸚鵡學舌,指責國內同志,這就與毛澤東發生了對抗。只是1936年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還未完全確立,王明在國際國內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澤東還無力與王明正面沖突,但是,王明的舉措已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為了防范王明影響的擴大,從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開始在核心層散布對 王明的不滿,[2-70]公開向黨內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跡,毛已預感到他在黨內的真正對手是王明。 注釋 [2-61]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62]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19—20、243;221。 [2-63]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頁244。黃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擔任組織部長,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接替叛變國民黨的原中央局書記盛忠亮擔任中央局書記兼組織部長,1935年2月19日黃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變」後獲釋,參加中共長江局工作。 [2-64]《中央關于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面軍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載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25。 [2-65]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發出的黨內文件《關于當前政治形勢》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處引文轉引自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K・庫庫什金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徐正明、許俊基等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32。此段引文的真實性可以從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名義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確定,該宣言激烈抨擊蔣介石「處處替日本帝國主義為虎作倀」,表示中共愿「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只是這份對外發表的公告沒有像黨內文件那樣,直接表明抗日應以中共為「中心」。參見中央檔案館編: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0冊,頁30、31。 [2-66]A・康托洛維奇:《是煙霧還是挑釁》,載蘇聯《消息報》,1936年6月10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論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91。 [2-67]參見A・季托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斗爭》;K・庫庫其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載《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70—72、334-35。 [2-68]王明:《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斗》(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紀念和中共新政策實行一周年而作)(又題為《新中國論》),見《共產國際》(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2-69]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必須保持同張學良的接觸」,但明確表示反對中共關于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打算。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于1936年12月16日致電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須「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沖突」,并提出「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于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以前對蔣介石采取的錯誤方針,敦促中共必須「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并且認為中共直至1937年1月還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參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70]Edgar Snow: Rcd superstar Over China(London: Random condo; 1979), P505.